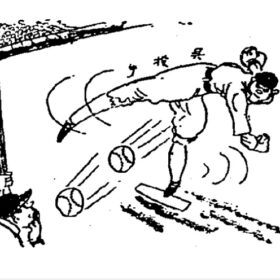林世煜,〈最長的一日 記林義雄先生家門慘變〉
(十周年追思文選)
最長的一日 記林義雄先生家門慘變
林世煜

林律師再也聽不到三個女兒的合唱了。恐怕奐均的獨吟,也要含著淚水才能聽下去。二十九日晚上,林律師在友人陪同下到仁愛醫院去探視病床上的女兒。林義雄爲了要以歡喜的笑臉面對奐均,在進入加護病房以前,先在護士休息室,抽了一根煙,等了將近十分鐘,強作鎮定,方始進入病房。
劫後餘生的小孩一看到爸爸,高興得眼睛亮起來。林律師愛憐地撫著相依為命的奐均,低低的說著:「爸爸對不起你們,爸爸原來希望帶給你們幸福,讓你們快快樂樂地長大,沒想到反而害了你們,爸爸對不起,請你原諒爸爸。」小孩定定的看著父親,用微弱但是堅決的聲音說:「我要像爸爸一樣勇敢。」
大人的眼淚一下子流出來,小孩却安詳的微笑著,一張小臉上溢滿了信任的神采。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軍法處要開調查庭,林太太和秘書田[秋堇]小姐一早匆匆地趕去景美。老太太已經出門買菜,奐均不久也上學去了。
林律師自從當省議員以來一直專心政治上的事情,律師的業務幾乎都停了。幾個月前才花半生積蓄,重置事務所,準備重新開業。沒想到他在去年底被收押,家境立刻拮据起來。林太太強忍著悲傷,到一家貿易公司當會計,而老太太也每天幫人燒飯,賺錢貼補家用。
老太太總是十一點多出門的,當時林太太和一些家屬正在軍法處憂急著調查庭不能完全公開,又想起兩個稚齡的小孩留在家裡,便撥了個電話回去,沒有人接。林太太擔心起來恐怕孩子溜出去玩了,要求田小姐回去一趟。正亂著,却宣佈退庭了,律師們走出來,大家一起去吃飯,菜上得很慢,等田小姐離開已經一點二十分。
田小姐昨晚睡得很遲,又累了一上午,直想趕快到林家大睡一覺,公車顛顛簸簸的,下了車都快二點了。她拖著疲憊的身子穿過巷道,天上還有些許陽光,到家,掏出鑰匙推開鐵門,又「碰」的一聲關上。客廳裡靜悄悄的、她喊:「奐均、奐均」一邊向臥室走去,一心要倒上床去,痛快的睡一覺。
主臥室的門開著,小奐均卷曲在床上,眼睛半閉著,大概玩累了。「奐均,奐均,起來吧,你吃飯了沒有?」田小姐一邊輕輕的推她,一邊喚著。奐均微微地睜開眼,虛弱的說:「阿姨,不要搖,我很痛,我受傷了。」「什麼」田小姐嚇了一跳,看看她却沒有跌壞的樣子。「奐均,你那裡痛,是怎麼了。」「有小偷拿刀子從我的背上刺下去,阿姨,我好渴。」田小姐低頭一看,驚得呆了,小奐均的學生服背上刺破了,裏面的白衣都翻了出來。「奶奶呢?妹妹呢?」「我不知道,阿姨,我好害怕,你不要走。」「奐均乖,阿姨不走,阿姨倒水給你喝。」田小姐一邊大聲講一邊跑出去倒水來,拿手帕沾濕了擦小孩的唇,又跑出去看對面雙胞胎的房間空著,趕快推對面奐均的房門,推開了,一看到紗窗被扯壞了,棉被堆在牆角,奐均的書包沾了血迹也掉在那兒,她急得很又出去推隔壁奶奶的門,門鎖著,她用力撞,踢,門一下躍開,奶奶不在裏頭。
奐均又呻吟了「阿姨、阿姨,妳在哪裡?」「奐均,不要怕,阿姨打電話,一下子就好。」田小姐撥電話給警察局報案,又打給她爸爸,爸爸教她送她去醫院,她沒有帶錢,打給幾家醫院都沒有救護車。打到一一九,救護車說馬上來。
「奐均,不要睡著了。」田小姐打了電話又趕快跑回臥室。「奐均,小偷怎麼來的?」「我不知道,是一個人開門的,他手上拿一把刀。」「奶奶呢?」「我好像聽到奶奶在叫我。」「在哪裏?」「好像在地下室。」田小姐又跑出去,往地下室樓梯的燈,怎麼不亮,黑漆漆的,她跑下幾級,矇矓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底下。
「叮——」門鈴響了,田小姐嚇了一跳。「誰!」「是我,康文雄。」她鬆了一口氣,是「亞洲人」的同仁來了。田小姐的爸爸一接到女兒的電話,就通知雜誌社,二位同仁立刻就趕過去,現在剛到,管區的警員也到了。(註:管區警員先到,亞洲人同仁才陸續趕到)
「怎麼啦!」「奐均受傷了!奶奶和雙胞胎都不在,康文雄,你到地下室看一看好不好。」康文雄走了幾步,就看到屍體倚在樓梯角。「秋菫,這是誰?會不會是林義雄的母親?」田小姐驚叫一聲,康文雄立刻上來。
同來的林濁水又迅速地走下去,他強忍著震驚和悲痛,攀著欄杆,避過死者,進入地下室,眼前的景像太可怕了,老太太卷曲在牆角,身邊流了一地的血。「康文雄,你來一下。」康文雄也踏進去,地下室光線很暗,兩個人心裏毛毛的,林濁水抓起一張小沙發,康文雄拿了兩個煙灰缸,林濁水把儲藏室的門撞開一條縫,兩個人看了一眼,看不出什麼,四面望了一望就準備上來。
「阿姨,我要媽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奐均乖,媽媽快回來了,阿姨送你去看醫生。」「我不要,我不要去看醫生。」奐均最喜歡電視上的小白兔卡通,田小姐靈機一動,安慰奐均說:「小白兔受傷了,是不是要看醫生,小白兔受傷了,我們送她去醫院,阿姨陪你去,乖!奐均!」警員進來了,大家都很吃驚,攝影師立刻準備拍照,隨後另倆位亞洲人的編輯同仁也趕到了。林濁水匆匆地迎上來「這不是普通的凶殺案,我要趕快通知林太太。」「她到軍法處去了。」「康文雄,你陪濁水去。這裡我們來照顧。」他們翻身走了。
一會兒救護車來了,鐵門太小,擔架進不來,忙了一陣,救護人員拿進來一張軟墊,和田小姐進入臥室。小奐均雖然受傷,蒼白的臉上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不要,我不要去醫院。」「奐均乖,阿姨陪你去。」客廳裏可以聽到她們的聲音。一會兒田小姐和救護人員把奐均抬出去了,留下話來說要送到仁愛醫院。
警員開始拍照,不讓別人進入地下室,怕壞了第一現場,到底死者是誰大家還沒有確定。攝影師就住在附近,他說大概是林老太太,大家還是不能肯定。一會兒來了一位街坊,他硬著頭皮下去一看,說不錯的,是她,我們認識的。是了,分局副主管說,她叫林游阿妹。大家都低了頭,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還有倆個雙胞姊妹呢?是不是被綁走了?」有人驚叫起來,現場剛來了林義雄的一位女職員,她們是不是上學了?她們是上下午班的。田小姐的父母也趕到了,我們打電話回雜誌社,請他們通知各人家屬注意安全,並請求警方保護,這麼一個特殊的日子,這麼一件慘無人道的凶案,怎麼不令人哀痛逾恆,我們再也禁不起另一件打擊了。絕不能容許再有人為了這個社會的政治衝突而犧牲。
張德銘和張政雄兩位律師趕到了,他們在門口碰到兩位從幼稚園回來的秘書小姐,雙胞胎今天沒有去上課,大家的心都沉下去。張政雄律師是林義雄的辯護人,如今又受林太太委託,全權處理這件慘案。另一位秘書蕭小姐也趕來了,她痛哭失聲。昨晚她和田小姐都在那兒陪林太太,今天早上還是她為奐均舖的床,如今被子被堆在牆角,上面染了幼兒的鮮血,她看了一眼就掩面大哭起來。
發行人司馬文武早就趕向醫院去。在那兒急診處的醫生正在全力施救。小奐均身中六刀,肺部胸腔嚴重受傷,大量失血,她還能活著,醫生們都覺得是奇蹟。整個下午不斷的爲她輸血,醫生和安全人員都紛紛捐血,消息雖然立刻封鎖,醫生們都知道了,他們義不容辭放下手邊的工作,要幫忙把林家唯一的骨肉,從死神的手邊搶回來。
奐均斷斷續續的醒著睡著,田小姐一面低低的和她說話,一面用棉花棒沾水爲她解渴,奐均嘴角抽動著,頻頻喚著媽媽,又問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
司馬文武到了,他和田小姐就一直守在奐均的身邊,主治的醫生,看了看失血的狀況,搖頭嘆息,田小姐又急得哭了。他們斷斷續續地問:「小偷是誰呢?」「不知道」,「你看過他嗎?」「不知道」,「好像看過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家裏看過?」「不知道」,「在家裡附近?」「不知道」,「是不是爸爸的朋友?」「不知道」,「媽媽的朋友?」「不知道」,「穿什麼衣服呢?」「穿黑衣!」是黑衣人!是黑心人!小奐均又睡過去了。
林太太在友人的陪同下也趕到醫院,她憂心如焚,「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不要讓義雄知道。」看到病床上的女兒,她痛不欲生,友人緊緊的抓著,林太太哭著喊著,昏過去。醫生趕忙為她調理,大家心頭一片黑暗,人間還有什麼事比家破人亡更慘厲呢?
在家裏,眾人忙成一團,偵訊人員正在拍攝記錄片,檢察官和楊法醫剛剛趕到,他們進入地下室開始驗屍。分局警員趕去衛理幼稚園,找到雙胞胎的學籍卡片,回來請蕭小姐辨認照片,提供她們的生活情形,預備開始搜尋。
地下室的燈不亮,修理了一陣,弄好了,檢察官和法醫下去了,先驗了林老太太,她身中十三刀,致命的傷痕是咽喉和胸腔。老人家面目全非,凶手是畜牲,是禽獸,是地獄來的魔鬼,我恨他,我咀咒他!
許久以後地下室傳來喊聲:「還有一個小孩在這兒,死了。」蕭小姐哇的一聲哭出來,衆人都呆了,一會兒,還有一個,雙胞胎都死了。這是滅門血案,是滅門!這絕不是一般的凶案,是謀殺,是要謀殺我們大家的身家性命,是要謀殺我們的幸福理想。我們心裏聲嘶力竭地喊著,憤怒和疑懼在噬咬著,大家寒著臉,緊握拳頭,一句話也吭不出來。

電話鈴又響了,是國際電話,辦案人員把話筒交給張政雄律師。對方是林義雄的友人,他說上午十一點多曾經打電話來,還是老太太接的。張律師把慘案告訴對方。正說著,人報康委員來了,他匆忙進來了,一言不發地走進地下室,看了一眼轉身上來,眼淚已經奪眶而出。張律師把話筒交給他。「是,我是康寧祥。我是康寧祥。不錯,慘案已經發生了。」康先生泣不成聲,嘶啞著嗓子,斷斷續續地說:「這是林家的不幸,也是全國、全社會的不幸,這件慘案發生在這個時候,更令人悲傷,我請您轉告海外的朋友們,在案子偵破之前,不要聽信謠言,不要輕舉妄動,我們要平心靜氣地承受這個苦難,我誠摯的要求你們和我一起遵守這個約定,不要輕舉妄動,千萬不要⋯⋯謝謝您們的關心,請您轉告其他的朋友。」話筒放下,屋裡寂靜無聲,康先生向辦案人員致意,又和張律師、蕭小姐交代幾句後,匆匆的又趕去醫院。
天黑下來了,林家的大人還沒有趕到,電話鈴又響了。是軍法處給張律師的,他放下話筒後說,「他們要我七點半去一趟,大概是要讓義雄保釋出來。」可是現場沒有親屬,張律師分不開身,又急忙打電話給同案的江律師,請他走一趟軍法處。
其實外頭一下午都忙著,朋友們趕到醫院探視林太太和奐均,又通知警察局保護被押者家屬,到了晚上7點,關中奉總統之命,到仁愛醫院,來向林太太表示慰問之意,並告訴林太太說:「總統下令讓律師保林義雄出來料理善後。」稍晚,果然就傳出林義雄保釋的消息,只剩下一些手續了,警總懸賞五十萬元捉拿凶手。整個台北偵騎四出,電視也播出來,震驚的社會,不能再容許黑暗角落中的暴徒,繼續逍遙法外。
仁愛醫院開刀房裏正忙著,一會兒裏面遞出一張條子來,要趕快找到臺大醫院一位胸腔專家。等在外頭的康寧祥抓起電話,撥醫院,撥市長、市議員,再撥到醫師家裡,他已經穿好衣服,立刻過來。他到了,直接進入手術室,稍晚主持開刀的仁愛醫院柯院長,控制了傷勢,手術完畢,將奐均送到加護病房,那時已經九點半了。
林家客廳的燈不知怎麼壞了,只有飯桌上點了一盞燈,大家在昏暗中沉靜著,突然門外響起淒厲的哭聲,林義雄的妹妹等人來了。「阿母啊!阿母啊!我不知啦!」哀痛不已的孤女哭喊著進來,親友們跟著把她按在沙發上,她掙扎著,哭喊著,「我不知啦!我不知啦!我要看媽媽,媽媽!媽媽!」她掙扎著捶胸頓足,蕭小姐流著淚緊緊地抱著她,沒有人能出得一聲。
男人們也來了,大家絞著手,臉色蒼白,輕輕的和張律師商量善後,牆上的佛像被取下來,好不容易安靜下來的婦人到廚房端來一杯米,把線香點起來插上去,願死者在天之靈安息吧!
準備保釋林義雄的幾個人,帶了林太太的印章、身分證趕到軍法處,張律師幫忙把死者移到殯儀館以後,也匆匆趕去,已經很晚了。軍法處一定要先把眞相告訴林律師,田小姐在一旁苦苦地哀求,請他們慈悲爲懷。好不容易才讓林律師出來,他一看到日夜懸念,以爲早都入獄的朋友全在那兒,滿臉的狐疑一下子掃開了。大家簇擁著抑不住興奮的他登車而去。
入獄七十七天的林義雄,顯得有點蒼白,帶著笑意的臉在路燈閃爍中微微發光。他頻頻問候友人,向他們致謝。車到了朋友家,早有許多人等著,大家寒喧了一陣,告訴林義雄是因為必須檢查身體,才保釋出來的。大家又把他送往長庚醫院去。他洗了澡,讓醫生檢查一陣,打了針。對著一屋子的朋友,高興得要喝啤酒,大家笑著陪他喝幾杯,又喝了點紹興,吸了煙,屋子裏漸漸地靜下來,氣氛也凝重了。林義雄漸漸覺得不對勁,待康寧祥躊躇地說出他母親被害,而大女兒傷重入院治療的眞象時,病房裡爆出林義雄痛不逾生的哀號,已經是廿九日凌晨二點了。
最長的一日落幕了。但是太陽什麼時候昇起呢?
第二天黃順興委員告訴他雙胞胎也遇害時,林義雄一滴眼淚也掉不下來。他死撐住全社會的苦難了。一夜不曾合眼的林太太也被接來了。夫妻乍然相見,恍如隔世,林義雄哽咽著,不敢說出雙胞胎的事。一旁的妹妹忍不住說了出來,林太太驚慌得瞪著一張張蒼白悲傷的面孔,當場又昏死過去。「只剩下我們三個了」林律師喃喃的說著。
下午到殯儀館,那樣的凄厲已不是人間任何字眼所能形容。一連串凶狠的打擊,不但使林家陷入絕境,每個人的心上也都有著千鈞的重擔壓著。
「爸爸!爸爸!」看到久別的父親,小奐均笑起來,眼睛也亮了。「爸爸聽說您受傷,從美國趕回來看你。」耐不住憂急的林律師,在中泰賓館經過一下午的休息之後,到晚上十點打起精神來看女兒,這是他僅存的骨肉了。「爸爸!我好了以後,要和妹妹去六福村玩。」可憐的女兒,她沒有妹妹了。「爸爸,我不要回鄉下,那裏沒有學校。」「乖孩子,那裏有的。」林律師強忍著淚水,愛憐的看著小小的奐均。「我要像爸爸一樣的勇敢。」大人的眼淚都流下來了。小奐均要像爸爸一樣勇敢,林律師無語問蒼天。他們夫妻父女要勇敢地擔起這個苦難。爸爸來探視,比給小奐均打了強心劑還有效,看到堅強的小女兒,林律師內心深處也湧起無限的生機。
這一天又要過去了。這漫長的惡夢仍然盤據在每個人的心頭,但是大家都從幼兒那裏感到無限的生命力。我們還是悲痛,我們還要承受許多苦難,然而看到那張洋溢著信任的小臉,我們知道,這最長的一日終要過去、明天,或什麼時候的一天,當我們醒過來時,太陽依舊會昇起。
本文輯自:
《十年生死——林游阿妹女士暨亮均、亭均受難十週年紀念集》(宜蘭縣五結鄉:慈林文教基金會,1991年),頁13-23,亦收錄於《落花春泥與新芽:林游阿妹女士百年誕辰 林亮均林亭均受難四十週年紀念文集》(宜蘭縣五結鄉:財團法人慈林教育基金會,2022年),頁43-49。
感謝慈林教育基金會惠允「台灣放送」轉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