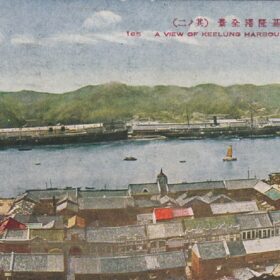四二四刺蔣事件的回顧與反思
黃文雄
(本文原載於2003年10月Taiwan News總合周刊第101期)
和今天這個研討會的其他場次相比,這一篇比較難以說是「論文」。第一,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單一事件,而作者本人是參與者之一。第二,作者意識到自己是以「史料」的身份在說話,因此寧可用「生平或biography如何碰上歷史或history?」的角度來報導描述和反思,希望在政治史之外,也能夠提供一些台灣社會史的史料。第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下文經常出現「我」字。
因為撰寫得很匆促,而作者在進出不同國的二十五年流亡過程中,為了安全考慮,極少留下日記或信件,題目中的「回顧」和「反思」必須從嚴(literal)解釋,此一缺陷,應先聲明。
一、留美學生的「Sputnik世代」
我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出國的。一九六〇年代的留美學生有些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特徵。
首先,五〇年代的台灣經濟尚未「起飛」;能留美的學生多半出自比較富裕的家庭,人數不多。到了六〇年代,經濟發展雖然累積了足夠的動能而被稱為「起飛」,但社會離相對富裕程度仍然還遠;可是卻有大量學生出國。其原因和美國的一項發展有關。一九五七年,蘇聯的人造衛星升空,在美國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有些史家甚至稱之為驚惶panic)。其結果是大學(尤其大學研究所)的擴充,而冷戰加溫加劇,利用獎學金從「自由陣營」的國家招收吸引優秀學生到美國留學,也成了冷戰的策略之一。拜這一發展以及其所帶來的獎學金之賜,只要成績夠好,一般家庭的子女也因此有了留美的機會。留美時,我曾戲稱這批留學生為「sputnik世代」。
第二,我們不妨考慮一下「sputnik世代」的政治社會經歷和環境。台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的屠殺和其後的「清鄉」以及「白色恐怖」後,一九六〇年的「自由中國」事件可以說是某種分水嶺。「自由中國」事件中出現的強力鎮壓,等於宣示了即使是體制內的溫和改革要求,在蔣政權眼中也是罪不可赦的「激進」。它所造成的恐怖氣氛對社會──尤其是比較關心公共事務的國民──有很大的震嚇效果。蔣政權之下的台灣從此進入了一個「超穩定」的時代。黨國機器完全宰制了民間社會。頭腦不肯停止思考的人開始考慮反反抗的另類可能。即使是敏感度較低的人,下意識中也感受到當時令人窒息的氛圍。用Hirschman的話來講,說話(voice)既不可能,唯有出走(exit)。留學變成出走的一種方式。(Albert O. Hirschman, Voice & Exit)。
第三,「Sputnik世代」所看到「後麥卡錫」的美國。六〇年代的美國是內戰以後最翻天覆地的一段時期,而掀起這個「青年革命」的正是美國校園的學生。這個世代的臺灣留美學生所看到的絕不只是「自由陣營」的首都美國而已,還見證了美國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新左運動、第三波女權運動的崛起、校園改革運動、「冷戰社會科學」(cold-war social sciences)的典範顛覆、新青年文化的「嬉皮」風潮……。
這個後來擴及全球(「超穩定」的台灣除外)的「六十年代」對這時期的台灣留美學生撞擊的程度不同,但是沒有「sputnik世代」的人能夠逃避當時的美國和蔣政權統治下「超穩定」的台灣之間的強烈而鮮明的對照。相對而言,我可以算是受到衝擊比較大而深的一個。
二、個人的留美經驗
一九三七年出生的我,從小就不是「乖囝仔」。幾乎從上學開始,就對學校的管教方式有很深的反感。小學(桃園國小)經常逃學到野外釣魚,初中在台北(市工)、新竹(工職)和嘉義(工職)讀過三家學校,退學、留級、記過都經驗過。所鬧的事包括揭發一個有貪污記錄的公民老師,所以這段時期的經驗似乎不能單純用「青春期的反叛」來解釋。以後就讀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表面上是「乖下來」,但在新竹中學時仍發生因為參加演講比賽被該校擔任國民黨小組的老師拒絕評分,以及劉自然事件時和同學乘機鬧事的事。而同一時期同班同學歐文港因為「義民中學事件」被囚禁過,以及亦師亦友的陳偉老師被捕,也增加了我的政治敏感度。
即使是壓力鍋也會冒氣。有壓迫就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反抗,包括無數個人的小反抗如初高中學生的反抗。我提到以上諸事,只是想寫下來作為研究台灣戰後社會史學者的參考。此外,我將略過大學(政大新聞系)和研究所(政大新聞所)的成長歷程,而只提一些和後來留美有關的事。
我因為對英文有相當的興趣,在台北的國際學舍有幾個外國朋友。尤其是其中叫Chuck的一位,常常給我有關美國的另類資訊。他推荐Galbraith的The Affluent Society作我研習英文的範本;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成立於一九六二的美國「學生民主聯盟」)也是從他口中聽到的。但他對我最有用的建議恐怕還是另外一件事。他說他在大學時觀察到留美的華人學生都喜歡黏在一起,一起租屋、買菜、做飯、上圖書館實驗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懷疑她(他)們見識到多少美國和世界?」他說。我聽從他的建議,留美期間,我雖然和台灣人的社區保持連絡,但始終和其他各國學生同住,而且有意識的隔一段時間就移動住所,藉此擴展交往圈子。這種做法對我的美國經驗(甚至我後來二十五年的流亡)有著相當的影響。
我一九六四年第一所就讀的是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匹茲堡原來以之出名的鋼鐵業和煤礦業吸引了許多移民和黑人,因此該城遺留著相當強的社會批判傳統:我第一個美國女朋友就來自有工會傳統的家庭。帶著在國內已有的反叛傾向,我很快地就開始接觸校內和校外的「課外活動」,包括民權運動、蘊釀中的反越戰活動和反核武運動。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當時當然沒有想到,但事後視之,我已經走了社會運動的不歸之路,一直到今天。
國內政治方面,我也開始探索。經過妹婿鄭自才(就讀同城卡內基理工學院)的介紹,我那年聖誕寒假,就去費城看了台獨運動的拓荒者陳以德教授和夫人Maxine。對台灣獨立的目標,我很快就認同,但對台獨的內容以及達成目標的策略,卻仍在探索中。但有一個方向卻已開始成形。學的是社會學,又見證到外國朋友的討論,我學會認真的區分國家和社會,並開始思考兩者之間的各種關係。這種思考背後,無疑有蔣政權完全宰制了台灣民間社會的陰影。那個假期裏,我也第一次對「社會力」有新的體會:碰到一個南方來的SNCC(民權運動的學生組織)的工作者。他穿的是南方黑人農民的牛仔工作服,全職工作,週薪只有十元美金。當時的台灣學生難免還保留一個特殊社會身份,這位這麼肯放下身段的學生,讓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匹茲堡的經驗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學習了黑人爭取民權的鬥爭經驗,白人社會的青年也開始了她(他)的反體制運動。前文說過,「學生民主聯盟」成立於一九六二年,這個組織後來成為運動最重要的力量。加州大學的「自由言論」(Free Speech)運動爆發於我到美國的一九六四年。次年又有第一次在華盛頓舉行的大規模反越戰遊行。等我轉學到康乃爾大學時,整個運動已經有波瀾狀闊的局面了,我的參與也越來越深。這個運動影響甚至擴及其他「第一世界」(包括日本)的國家。而在同一時期裏「第二世界」的共產國家也有各種動盪,其高潮是一九六八:美國的詹森總統放棄連任(未熟知越戰的年輕世代,也許看過湯姆克魯斯的「七月四日誕生」),捷克有「布拉格之春」,在法國則有戴高樂被學生和工人聯手逼退。不但如此,第一與第二世界的動亂也讓兩者比較無餘暇他顧,第三世界的國家和社會也因此有較大的行動空間,再加上受到越南人民的鼓舞,各種「人民解放運動」(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s)彼落此起。當時台灣尚屬「第三世界」,我也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待台灣海外運動的。
全球狀況如此,相比之下「超穩定」的蔣政權下的台灣卻近乎一潭死水!台灣不只援助南越的獨裁政權,為美軍維修軍機,還成為駐越美軍渡假樂園(台灣的色情工業就是在那時「起飛」的!)。比較敏感的臺灣學生都無法對這種鮮明的對照視若無睹。
這裏不是分析和評論「六〇年代」這段世界史的地方。我想指出來的是,在「Sputnik世代」的台灣留美學生中,我對這場運動的參與雖然可能相對最深,但身處那個時期的美國,沒人能完全不受影響。這是海外運動的背景之一,值得歷史學者賦予更多的注意。
同理,這也是刺蔣案的背景之一。有人謬讚我刺蔣的勇氣時,我的回答經常是:「當那麼多國家的朋友組織起來,上了街頭,有人甚至回國打游擊,刺蔣在當時的感覺,其實並不那麼特殊」。比較了解「六〇年代」的人,應該會相信這段話並不純粹是謙虛之辭。
三、刺蔣的考慮和準備
蔣介石之培養蔣經國,在尚未亡命台灣時就開始,但他的家天下的接班設計,應該是敗退台灣後才具體成型。一九五〇年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排除了「蔣家天下陳家黨」的CC系。以後政府事務雖然以陳誠為首,但威權獨裁政權權力關鍵的特務和政工系統卻全歸蔣經國。蔣經國掌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橫跨黨、政、軍,有「地下朝廷」之稱。白色恐怖當然也就是在他指導之下進行的。其後他繼續縱向橫向的擴權竄升。一九六五年陳誠逝世後,他已經完全掌控了黨政軍,雖然在刺蔣案發生的一九七〇年他名義上只是行政院副院長。
在「自由中國」事件後令人窒息的「超穩定結構」下,連內在的思想自由都要被壓制,任何形之於外的活動自然更無可能。有些人開始有暗殺蔣經國的念頭。正如「世界人權宣言」的前言所說,「鑒於為使人類不得已而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和法治受到保護」。人權和法治在蔣政權之下既然不獲保障,自然會有人民想行使其反叛權(right to rebel),而暗殺正是行使該權的方式之一。不只國內有人這樣籌謀(最近史明前輩就提到一件個案),蔣經國數度訪美(一九五三、六三、六九)也在海外運動某些圈子激發有關暗殺他的討論。
如前所述,我出國的第一年就在鄭自才的引介下參加了獨立運動。第二年因為KMT校園間諜密告,上了黑名單,因此也曾參加了一些討論。那時的留美學生還不能擺下知識份子的身段,有些人主張僱用黑道或黑人執行暗殺,讀理工的則偏向從技術觀點著手(如高級遠距狙擊步槍)等等,這個方向的討論和我當時的運動經驗與思考方式很不一樣,因此談歸談,興緻不高。直到鄭自才和賴文雄找我去紐約(康大在紐約北部綺色佳)商量台灣人自己去做,我才認真起來。
一九六九年蔣經國第四度訪美。不久之後,就有他即將五度訪美的傳說,我也從一位擔任國會議員助理的康大同學那裏聽到了如果他來,會「高規格」接待的消息。「有一個我不完全了解,也不能告訴你的twist」,他說。我後來才領悟到,所謂「高規格接待」是尼克森和季辛吉早已計劃要和北京交往,因而事先佈置佈置的撫慰。消息確定後,我們四個人(鄭自才、賴文雄、我妹妹晴美和我)開始進行具體的計劃。
我因為人在康大,大部份的具體準備工作(如買槍借槍之類)由鄭自才和賴文雄安排。我自己反而用較多時間來思考暗殺蔣經國的政治意義。自己分析之外,我還和兩位外國的死生之交商量。那時我參加了好幾個激進運動的圈子。和外國同志商量,不只是為了印證檢查自己的分析,也出於我對這些圈子的承諾(commitment)。只告訴生死之交的兩個人,則是為了保密。
那時不少活躍份子都多少左傾,這兩位朋友最初都反對我的計劃,認為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行為。照那時運動者之間的習慣,我們辯論了好幾個星期。我甚至把自己的論證寫成文字。論證的要點如下:
第一,雖然必須使用武器,暗殺蔣經國的首要意義還是政治性的,因此必須由一個普通的台灣人去做,才能凸顯其政治意義。找別人做或遠距離狙擊步槍之類的匿名攻擊(見前文),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國傳達這個訊息:台灣人既不接受蔣政權的少數統治,更不接受蔣家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設計。
第二,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的繼承機制已經以民主規範制度化的國家,暗殺將沒有意義。(甘迺迪被暗殺後,詹森馬上接任,國家機器依舊持續運作)。但台灣不同,ROC形式上仍是共和國,為了取得正當性,蔣家父子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為小蔣的接班舖路。除去了蔣經國,國民黨雖然不會就此崩潰,但黨內的權力鬥爭必將再起,這就可能鬆動當時「超穩定」的家天下的黨國統治結構,替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某些可能性。
第三,對當時相對沈寂的反對運動可能有某個程度的鼓舞作用。
第四點則和我作為反對越戰運動的一份子有關。美國政府口口聲聲自由民主,卻在全球各處支持殘暴的獨裁政權,包括蔣政權。如果不合美國的利益,第三世界國家即使極為溫和的政經社改革(如一九五〇年瓜地馬拉的土地改革),也會招致華盛頓的干預和顛覆。這使得第三世界的國家除了依附美國或蘇聯之外,沒有在兩大帝國之外獨立探索自己的道路的空間。越南(就像革命初期充滿多元活力的古巴),就是這種陷阱的犧牲品。蔣政權在越戰中既然是華盛頓的幫凶(見前文),我也希望任何有削弱蔣政權可能的動作,有可能(即使只是可能)有助於越南人民的獨立戰爭。
我就這麼以上述的論證說服了自己和朋友。
四、刺蔣經過
四月二十一日蔣經國飛抵美國。之前我們四個人會商行動的細節。本來是說好由我、賴文雄和鄭自才抽籤決定誰去開槍,但鄭自才是我的妹婿,和賴文雄一樣,有妻子兒女,我很早就決定由我去執行比較合理(外國朋友行前也已替我辦了告別的party)。開會時也就如此商定。二十一日我們都和台獨聯盟的成員以及其他同鄉去蔣經國下機的安德魯軍事機場「迎接」,大家的目的當然是要給他下馬威,我則另外有觀察保護他的護衛安排的目的。
蔣經國在華盛頓停留了兩天。接待果然是高規格的。雖然只是行政院副院長,卻是國家元首的待遇,不只總統尼克森親自接見,季辛吉甚至到他下榻的布萊爾賓館移樽就教。當時外人都不知道尼、季兩人已經和北京秘密接觸,高規格的接待是有意的事先佈置,希望在事情公開後有「撫慰」小蔣和國會親蔣議員的作用。
蔣經國在華盛頓之後的行程是二十四日在紐約的廣場飯店(Hotel Plaza),向「東亞—美國工商協會」(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發表演說。這也是我們選定的時地。我之前已經到飯店偵察過貴賓座車的進出途徑。前一天(二十三日),我和妹妹晴美更到飯店入口和周圍走了一趟。考慮到有必要躲開「暗椿」便衣人員的監測,我們決定了一條接近的路線。飯店位於五十九街和第五大道交口的東南角。飯店入口不在中央而比較靠近五十九街,前面有一個噴泉廣場。廣場也是台灣人次日將示威的地方。廣場和入口應該是護衛人員的注意焦點。可是飯店的後側和左側各有巷子。後側的巷子有一幢建築正在整修,比較凌亂。我們決定次日從五十九街走入後側巷子,轉到左側巷子,然後從那裏沿飯店的「亭仔腳」走向入口地區。這一邊的警衛措施可能比較鬆懈。
四月二十四日那天,照原來的計劃,槍放在晴美的皮包裏。我、她和賴文雄按原來計劃走向飯店。沒想到走到飯店後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時卻被建築工人和警衛擋住了。這不是論理的時候,我們決定多跑半條街轉入飯店右側的巷子,當晴美在飯店的南角把槍交給我的時候,蔣經國的座車正好由五十九街轉入飯店入口前面。
如我預料,我這邊的「亭仔腳」果然沒有護衛人員。護衛人員都在旋轉門前排成兩行,蔣經國正走入這兩排人形成的「甬道」。「甬道」不長,我很容易的就衝到他身邊約兩、三公尺的地方。
這個做法需要一點解釋。前文說過,我認為雖然必須使用武器,但暗殺的動作還是個政治行為。如果誤傷無辜,即使技術上暗殺成功,必然會傷害此舉的政治意義,對運動有害。可是要避免傷及無辜,必須儘量接近對象,而接近對象也就是接近對象的衛護人員,這是個政治難題,不是只須考慮技術的好萊塢電影。因為為前述多跑半條街造成的延遲,我接近時他正在旋轉門外,即將進入,可以說是最後一秒的機會。沒預料到的是,我開第一槍的時候,一個機警的紐約警官(detective)看到了,飛身而起把我的手肘往上托,子彈飛向蔣經國頭部上方。我開第二槍時,蔣經國已經進入旋轉門的右側了。而我也被一大「堆」警察壓在地下。這時,場面變得有點「鬧劇化」。我個子小,可以從那些彪形大漢的身體間鑽出頭部或上半身來。每一次這樣時,便會有其他警察飛身壓在我身上。我相信是這個場景,使本來在示威隊伍中發傳單的鄭自才一時衝動,跳進來救我。雖然這不是理性的做法,他出自衷心的關懷,還是非常感人。(在此附帶一筆,有些報導說,他身上帶著刀,這是沒看法庭文件的編造。)
我和自才被帶上手銬時,正在示威的幾十位同鄉從驚訝中回神過來,口號喊得特別響亮。
五、訊問、拘禁與同鄉的救援
我和鄭自才被送到警察局後,就被分開了。審問我的人包括紐約警方和聯邦人員,這兩批人之間似乎有某種的競爭和敵對。我參加過當時美國包括民權運動的幾個社會運動,對我應有的權利還算熟悉。警方第一個想知道的是我是誰,住那裏:我身上故意不帶任何證件,警方無從查起。而我最關心的卻是我的女朋友。為了保護她,我沒有告訴她刺蔣的事,而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可能到我住處找我。我必須把時間拉長,讓她和可以照顧她的朋友在警方搜索我的住所之前,有機會先在電視廣播上得到警告。
警方看我有備而來,不肯說出姓名和住所,就開始引誘我說話,問我有關台灣的事。這我倒是很高興和他們分享,但只要問話一移向我個人,我就很禮貌的「礙難合作」。有一度他們軟的不成,改用硬的,例如推我一把之類,但我警告他們我絕對會有很好的律師,以及明天刺蔣的事一定上紐約時報的頭版時,他們就有人出來扮白臉了(這個事件果然上了紐約各報的頭版)。我一直到斷定新聞一定已經傳到康大時,才說出我的姓名、學校和地址。
訊問之後,隨即在法院被以「謀殺未遂」(attempted murder)和共謀(conspiracy)起訴,起訴後,我們被送到紐約市拘留所。拘留所是一幢高大的老建築,綽號「大墳」(the Tomb)。在相當冗長的入獄程序(processing)中,我見證到反越戰運動的影響力和它如何影響許多人對第三世界國家反對者的同情和支持。在好幾個站都有工作人員的特別照顧,而且消息傳得很快,行經之處,都有人舉起緊握的拳頭打招呼,這是沒有經歷一九六〇年代的人很難想像的。送入囚室後更來了一群政治犯。很快他們都變成朋友,包括反戰運動、黑人解放運動和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的成員。我加入了他們的政治讀書會和討論會,整天討論辯駁,坐牢的日子過得並不寂寞。
在牢外,留美同鄉會很快在台獨聯盟的主導下組成「黃鄭救援基金」,向同鄉募款作保釋金及律師費用。由於事涉聯邦事務,保釋金訂得很高,我十萬美金,鄭自才九萬(這是一九七〇年的美金)。據律師說,這很可能創了紐約市的記錄。雖然當時大多數的同鄉都是靠獎學金生活的窮學生,同鄉的反應意外的熱烈,捐款的人本省外省籍都有,兩個多月就籌足了。鄭自才家有妻兒,先出獄,我則多待了約一個月。
康乃爾大學是長春藤盟校之一,有不少校友到國會和聯邦政府工作。她(他)們之中有好幾個人事後告訴我,有好幾個官員和議員都說我們能因捐款熱烈而被保釋,等於是對蔣政權的少數統治和獨裁統治的一場另類「民意調查」,一場布衣菁英的「民調」。我開槍的動作雖然比較富於戲劇性,但這場「民調」對美國政府的影響和對國民黨的衝擊,相比而言,反而更大。參與這次「民調」的人還有待歷史學者的研究和肯定。
聯盟最初聘請的律師似乎較少處理政治性案件的經驗。我和鄭自才出獄後,開始另找律師。我們最後決定了三個人。第一個是Leonard Boudin。他是一位極受尊重的進步律師,辯護過很多改革者和革命者的案件(他自己的女兒當時也因為反戰被聯邦政府通緝中)。第二位是Victor Robinowitz,前一位的合夥人,也極為同情被壓迫的人民。第三位是檢查官出身的Nicolas Scopetta,當時是Cyrus Vance(前國務卿)所主持調查紐約市警察貪污委員會的律師之一。其他幫忙的人,還有我在康大的教授Jay Schuman,一位社會學家。他有一套篩選陪審團的方法,在幾個「運動型」的案件裏,對辯方律師助力不小。
我們和律師商量的結果,訂下了幾個基本策略。第一是拉長審判過程,讓鄭自才和我還有案件本身有較多時間為海外運動從事宣傳工作。這點做得很成功,審判一直拖到次年七月。第二是為有妻兒和並未開槍的鄭自才尋找減輕判刑的途徑。第三,為我取得儘可能輕的判決。從司法的觀點看,前途並不樂觀,因為鄭自才向陳榮成(路易斯安那州大教授,負責台獨聯盟的島內工作)借的槍是登記有案的。檢方找到了他,逼他為檢方作證。唯一的辯護空間是我和鄭自才的套招。我在後來案件發展越來越不利時,在審判的後半段自認有罪(「在全力扶持蔣介石獨裁政權的美國之法律下,我自認有罪」),希望有助於鄭自才的部份。但檢方掌握的不利證據很多,最後還是幫不了他。
法官決定在七月宣判。我們兩人面對坐牢或棄保逃亡的抉擇。我們都選擇了後者。我透過同志和朋友(包括三位同鄉)的幫助逃離美國。為了讓鄭自才先出境(如果我先出境失敗,可能會引發全國警戒。我總是想著妹妹晴美和外甥外甥女),必須控制好時間,難度很高。這三位同鄉的效率,讓我被FBI監視下執行潛逃計劃的外國朋友都另眼相看。這是一個我報廢之前必須好好寫下來的故事。
我從此走上了二十五年流亡各國的道路。
六、有關刺蔣案的爭論和爭議
(一)我為甚麼選擇棄保逃亡?
有些同鄉認為我應該遵守美國的法律,好好去服刑坐牢(十五年),才是「真英雄」(有位同鄉還著文說,「否則就是狗熊」)。我尊重他們的看法。但我必須承認,我一開始就沒有坐牢的想法,反而案發僥倖未死(「僥倖」是因為蔣經國的衛護人員可能察覺了先開槍)後,就開始計劃走入地下。其理由用白話講是這樣的:在全球各地扶持獨裁政權的美國政府是蔣政權的大老板。我既然有理由對小夥計開槍,也就沒有理由在還有選擇時去乖乖遵守大老板的法律坐牢。除此之外,逃亡並不表示要放棄運動。例如,以我多年參與國際運動所建立的聯繫,我在流亡時還是有為台灣做事的許多可能性,雖然這些是台灣人近年才開始知道注重的國際社運關係與其他NGO關係。
另外,作為一個學社會學的人,我從來不認為我是甚麼英雄。回國後,我也一有機會就在各種場合文章解構「英雄」的個人主義意涵。在不平常的時代和環境裏,總會有許多平常人做出她(他)們平常不會做的非常事,否則世界上就不會有革命,台灣的民主化時期也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走上街頭了,我只是這許多平常人之一。因此,與其說個人的「英雄」,不如說非常時代的集體「英雄現象」。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其時代和社會條件,這是本文在一開頭就從時代和社會背景講起的原因。
(二)台獨聯盟在刺蔣案後的分裂
那時台獨聯盟成立未久。刺蔣案發生後,馬上面對一個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是道義和推展運動的需要,使聯盟必須貼近我們四個人籌劃執行的刺蔣行動。另一方面,聯盟成立未久,有些組織成員擔心台獨聯盟被美國列為暴力組織並危及個人生涯,因此必須和刺蔣保持(在美國政府眼中的)某種距離。這是個不難了解的兩難之局。觸發爭議的是聯盟使用部份「黃鄭救援基金」,僱了一位叫Victor Louis的律師到華府做遊說,希望美國政府不會把聯盟列為暴力組織。任何組織都會有的路線爭議因此浮上檯面。反對這種遊說必要的人認為聯盟自稱是革命組織,甚至倡言武力革命,沒有必要怕被宣佈為暴力組織,而我們四個人自己籌劃執行,已是保護組織的做法。爭議(包括我和鄭自才應否逃亡)難決,加上原來已有的思想差異,後者這批人後來退出了聯盟。
宏觀長期而言,這次分裂的後果並非完全負面。分裂後的聯盟必須吸引新血以補充實力(這批新血後來又脫離聯盟組成了台灣革命黨)。退出的人另外開創多條道路,加上國內發展(如中壢事件)的刺激,反而開創了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海外運動百花齊放的多元興盛局面,發揮了更大的影響力,雖然反動運動的重心已經逐步移回國內了,而運動中心移回國也正是海外運動的每個成員所夢寐以求的。
七、最後的回顧和反思
(一)一九七〇年的四二四刺蔣事件,必須同時從「Sputnik世代」留美台灣學生的五〇年代國內經驗、六〇年代令人窒息的蔣政權「超穩定」統治和他們在六〇年代的美國經驗去看,才能得到比較完整的了解。
(二)黃文雄的開槍和鄭自才的被捕只是比較戲劇性的象徵。對美國的影響和對蔣政權衝突較大的,恐怕還是海外「布衣菁英」捐款援救黃鄭的那一場「民意調查」。
(三)一九七〇年刺蔣案後,次年ROC就被趕出了聯合國和安理會,蔣政權因此失去政權正當性的一大支柱。這使得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新人新政」的包裝,必須面對原來的少數統治不能長久持續的問題,其結果是開放較多本省人進入黨和中央權力結構。但這只是沒有和民主化同時進行的「本土化」,因此後來還是有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和林家血案、陳文成血案和江南血案。真正的民主化過程還是要等待後來有八〇年代至九〇年初的人民抗爭、國際壓力以及統治集團內亂等等因素的交互聯合作用,才產生較有實質的結果。四二四刺蔣案在這一連串發展中的角色和因果比重仍然難以釐清,還需要歷史學者的仔細分析。
(四)歷史長河的流向、逆流和潛流極端複雜,即使是數十年的台灣戰後史,或其中單一事件如刺蔣案,仍有待史家的持續追蹤和解剖。本文已經夠長,有些回國後的思考無法列入,請參閱附錄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一文。
八、附錄:蔣經國與蔣經國現象
(作者前記)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政治轉型的各國之中,台灣有一個特別突出之處。反對運動雖然能夠迫使蔣政權從事某些改變,但國民黨繼續執政到二〇〇〇年,民主化的方向、步調、內容和範圍,仍大體由國民黨主導,充滿了延續政權生命的必要所驅使的「適可而止」的工具性。我們從來不曾真正和威權的過去告別。所謂寧靜革命其實是一場諸多基本改革猶未開始的非革命。中正紀念堂的依然聳立就是一個極富於象徵性的見證。新政府三年來包括新憲法等改革行動所面對的阻力,也告訴我們「寧靜革命」的有限性。
在這種狀況下,復辟勢力重新抬出蔣經國神位的政治動作,雖然並非不可預期,仍有加以解析的必要。因此將這篇拙作附於文末,作為本文的一個腳註。
泛藍陣營最近利用現代廣告和公關技術所刻意營造的「經國風」,在道德上、知識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場墮落不堪的鬧劇。分析起來,主要的手法有兩個。
第一個手法是把蔣經國抽離歷史的脈絡,利用社會殘餘的封建價值,塑造蔣「愛民如子」的形象,把他的生平個人化、「行誼化」、「德目化」,好像蔣經國時代只是他個人人格的外顯。這種新聞學上所謂「人情趣味」(human interest)的技巧,正好可以用來規避許多尷尬的歷史事實,例如蔣經國情治頭子的過去,他在二二八、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和象徵國民黨連最溫和的改革也不能容忍的「自由中國」等事件中的角色,以及蔣家父子為了完成他們皇朝接班的設計所進行的黨內外權力鬥爭,等等。
然而,有兩個歷史事實是這種手法也不能忽視的。第一是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第二是結束威權獨裁統治的民主化。如果不能讓蔣經國在這兩個史實上沾光,第一個手法所想營造的形象不論如何感人,所想規避的史實不論掩蔽的如何巧妙,終究將失去和後威權時代台灣的相干性。所以,第二個手法是儘量把蔣經國和本土化以及民主化聯繫起來,甚至說成是他的功勞和成就。
這第二個手法如果成功,有至少兩個好處。第一,如果有人不為建立於封建價值的「人情趣味」所惑,第二個手法仍然可以主張蔣經國不管早年如何,至少在晚年「也做了些好事」。第二,如果手法成功,泛藍這個復辟意味極濃的「歷史重建」,還可以帶上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光環,而泛藍理所當然的正是這個光榮法統的繼承人。
既然前一個手法的相干性是建基於第二個手法所想達成的目標,我們不妨針對蔣經國和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關係,稍作分析。
蔣經國能和結束少數統治的本土化扯上關係,主要靠的是他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後,容納部份的本省「菁英」進入黨國權力結構的事實,也就是所謂的「吹台菁」。這是甚麼樣的一種本土化?
像任何沒有失去常識的獨裁者,蔣家父子並非不知道少數統治必須用某些「本土化」的措施來維持和加強。容許地方選舉,並且用「特許」某些經濟利益(這是黑金的起源),以換取本土勢力自甘跼限於地方而不企圖爭取進入權力中心,即是這種「本土化」之一。然而進入1970年代,內外情勢開始變化。1970年的刺蔣案首開其端。黃文雄開槍的事雖然因為其戲劇性而較引人注目,但對蔣朝和華盛頓最大的衝擊,還是留美的台灣學生很快就湊足十九萬美金的保釋金的事實。當時留美學生絕大多數都是靠獎學金生活的布衣「菁英」,這場前所未有的「民調」使美國政府都不能不再次警告其所卵翼的國民黨:必須適度的開放政權(這是「吹台菁」背後的壓力之一)。
隨之而來的是次年ROC被踢出聯合國的事實。會員國和安理會的席次是國民黨裝扮其統治正當性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其衝擊不輸必須「處變不驚」的地震。1970和1971這兩件接踵而來的事件都逼使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而實質形式接班的蔣經國,不得不進一步「本土化」。借用王景弘先生「香腸策略」的比喻,是多切一片出來餵食安撫被排除壓迫的多數。很明顯的,這是沒有和自由化與民主化隨伴而行的「本土化」,事實上是一種強人恩賜式的收編,長期而言固然會有促進本土化的客觀效果;但短期而言,其動機與後果都是當時獨裁威權體制的增強。若非如此,我們將如何解釋後來包括美麗島事件以及林宅、陳文成和江南等血案的那最後一波血腥鎮壓?
蔣經國和民主化的關係也值得稍加考究。首先,我們必須區分政治學常識裡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日常語言裡所說的「鬆綁」,很多獨裁政權都會在非不得已的時候採取鬆綁的策略,以舒解國內和國際的壓力。鬆綁的程度甚至可以包括容忍反對黨的出現,只要國家權力還是在統治者的掌控中。這種自由化雖然在某些條件下可能有助於或導致民主化,但並非必然如此,兩者必須加以區分。
不妨看看蔣經國在1979年到逝世前的處境。美麗島事件和其後的血案並沒有讓人民失去抗爭的勇氣。不但政治反對運動屢仆屢起,社會運動也出現了。工商界看在眼裡,同時又要為著他健康狀態的起起落落擔心,也不敢放心投資,雖然當時的台灣有傲視全球的資本儲蓄率。
國際情勢也對國民黨政權不利。江南案牽涉到蔣孝武,使蔣經國不得不向美國媒體宣佈蔣家人不會接他的大位。在隔壁的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被人民推翻。在全斗煥的南韓,甚至蘇聯帝國和中國等不少地方,也有和人權和民主相關的騷動。這些後來導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發展,使得第二任的雷根政府也不得不節制第一任時對其卵翼下獨裁政權的縱容。(在國際關係和人權史的文獻裡,這被稱為「雷根在人權問題上的翻轉」Reagan’s turnaround on human rights)。即使蔣經國看不清這些,華盛頓也會傳下這個消息。
事實上,蔣經國是一個極為精明的獨裁者。他嗅到「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在變」。為了他的家族,為了他的黨,他毅然決定進行自由化的鬆綁,容許民進黨成立並隨後解嚴;不像某些獨裁者那樣不計代價、玉石俱焚的鎮壓到底。為了讓其他的獨裁者學他的榜樣,對這點,我們應該加以肯定。但是把這種自由化和民主化等同,有如泛藍陣營和右派學者所為,卻是存心模糊化並繼之以硬拗的墮落。
我們不妨看看蔣經國1988年逝世時所留下的佈置:小鳥籠的戒嚴拿掉了,但是解嚴之前已經裝置了一只大一號的鳥籠:國家安全法;李登輝這個虛元首,由掌黨的李煥、掌政的俞國華和掌軍的郝柏村環伺「輔佐」。這活脫是一個自由化的佈局。如果李俞郝能同心共濟,僅限於鬆綁的局面至少也會再維持一段時間,其間台灣也將只不過換上一個尺寸較大的鳥籠而已。事實上,李俞郝之爭權失和也一直是泛藍人士的椎心之痛。
台灣的民主化其實是在國民黨分裂之後才開始有其實質的。李俞郝之互爭給了李登輝脫離虛位元首及黨首之命運的機會。其後在國民黨內部分裂的過程中,民進黨終於取得較好的成長發展條件。蔣經國佈置的政權衛護者終於失勢,也使國安法等佈置失去了「牙齒」。就主觀設計而言,這些發生時,蔣經國早已去世了。就客觀後果而言,如果把因果鍊拉長而說蔣經國對台灣的民主化有某種貢獻,他的貢獻恐怕還遠不如新黨和郝林(洋港)陳(履安)。這是歷史上常見的通律。在因果力的比重上,統治集團自身分裂的貢獻幾乎都大於革命或改革力量的貢獻。但我們不能說蔣經國曾期待國民黨的分裂,我們也都知道泛藍最恨李登輝的是甚麼。
以上是我個人對蔣經國和台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的分析。讓我以兩點作結。第一,泛藍勢力為蔣經國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所聲稱的蔣經國對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貢獻,並不經得起比較仔細的分析。第二,這是我個人的偏見,單單談本土化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只有徹底的,全面的,包括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民主化,才是真正的本土化。而泛藍勢力改寫歷史的企圖,只不過進一步曝露其幾乎不受任何標準規範的反民主的反動性格。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22/06/28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