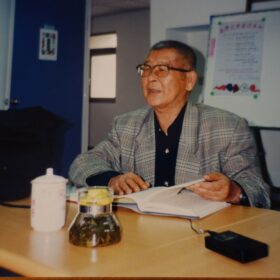鄭南榕的路、我們的課題、台灣史的未來
周婉窈
(原發表日期2013/4/25)

本文係作者應「第七屆蔡瑞月舞蹈節Forum文化論壇2013」之邀而寫,刊於財團法人台北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發行的《焚而不燬台灣魂自由之路開拓者與殉道者鄭南榕》一書中。承蒙曹欽榮先生指正,謹此致謝;本文略作補充修改後,轉載於此。(周婉窈 2013/06/07)
李敏勇先生邀請我來參加本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起初我是有所猶疑的,我說,我並不認識鄭南榕,誰和誰真正認識他。 李先生說,他已經邀請幾位熟識他的人士,他希望我能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我想一想,好像也還可以,於是就答應了。宣傳海報上派給我的題目是「從歷史的面向看鄭南榕其人其事」,不過,我最後的題目如上。歷史無法給固定下來,它和過去、現在、未來往往處於一種交互作用的浮動關係,在台灣戰後近六十八年的今天,我們無法不墮入沈思:鄭南榕選擇的路,何以還是充滿荊棘?我們要如何往前走?
說我不認識鄭南榕,不完全準確。我在讀碩士班時,其實見過鄭南榕,應該就是一九八○年年底周清玉女士代夫(姚嘉文)出征競選國民大會代表的時候吧。當時在政見發表會的會場,有一位年輕人,穿著背心,上面寫著「選舉無罪」四個大字,在人群中穿梭,非常醒目。友人說:那是鄭南榕。當時他並不在「黨外」的圈子內,但好像大家都知道他。就這樣,鄭南榕獨特而孤單的身影就留在我的腦海中。不久後我出國求學,後來因為我先生的工作,遷居加拿大溫哥華。一九八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和我先生參加台灣同鄉會的活動,突然間,有人以很嚴肅的聲音宣布「 鄭南榕先生自焚過世了」,頓時會場氣氛變得很凝重哀淒,大家站起來為他默哀。這是在那個時點為止,我對鄭南榕的認識,也可以說其實是不認識的──要真正認識鄭南榕,必得認識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台灣。
我從一九八一年出國求學,一直要到一九九四年才返回台灣定居。在台灣從解嚴到刑法第一百條修正,台灣享有思想自由為止,這是政治社會運動最激烈、最昂揚的五年(1987-1992),我都錯過了。我對鄭南榕、詹益樺的認識,都是回國以後自己補課,慢慢有個了解。二二八、白色恐怖也是如此。最近讀《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行動思想家鄭南榕》(台北:書林,2013),凝視解嚴後前後三年的政治運動照片,深受感動,但感觸也很深。個人錯過一個昂揚、壯烈的時代,不足惜,因為那只是個人沒有那個因緣;重要的是,我們曾有過那樣的一個時代!曾經有一位多數人不認識的跑船的年輕人,詹益樺,他在鄭南榕的送葬行列行進中自焚,才三十二歲,他生前寫道:「鄭南榕是一個美好而偉大的種子,而我也想當一個美好而偉大的種子。」「人民有權革命罪惡政權,必要時,以人最高情操『解決自己生命』對抗他。」前一句讓我們反省:為何我們沒讓種子長出應該長出的東西;後一句讓我們想起圖博(西藏)人自二○○九年以來已經超過一百人自焚了。
去年一位新聞系的老師很感慨,跟我說:竟然有新聞系學生不知道鄭南榕是誰!我們的新聞自由是怎麼來的?!二○○八年解嚴後第二次政黨輪替,由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其後很多指標都顯示:台灣的自由度不斷在減縮,威權時代的許多現象都重新彈回來。這個情況讓我們警覺到台灣社會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正在退轉中,也讓我們不得不面對「威權體制舊勢力正在反撲」的嚴重問題。我們不得不問:何以威權舊勢力可以這麼輕易就反撲?對此,我們該怎麼辦?
以下我想從「歷史情境的掌握」來提供一個理解戰後台灣歷史的角度,透過這樣的理解,或許我們更能掌握鄭南榕等人的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並且了解我們的路何以這麼艱辛,思考未來怎麼走。
「歷史情境」不是很容易掌握的,牽涉到很多層面以及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我越研究歷史,越感覺到歷史很難。我們將所有文獻都看過了,條列出各式各樣的因果關係,真的就了解歷史了嗎?我認為,最難的還在於如何設身處地地去體會當事人/人群所面對的「情境」,並了解這是正在成長和以同樣速度正在老去的社群全體所一起歷經的時間,而在這時間框架內是有實質內容的。這種掌握要求神入(empathy),也同時要求鳥瞰式的、加入時間深度的全觀點。
我之所以會提出「歷史情境之掌握」,乃是因為在研究霧社事件的過程中,我發現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以及激發事件的直接原因,無法讓我們貼近當事人/人群在大變動後所面對的情境。舉例來說,一般推測莫那魯道死時四十八歲,他的部族在他二十四歲時歸順,之後到事件發生剛好也是二十四年,在這段期間他處於怎樣的情境?他的部落/部族在他二十四歲前擁有什麼?之後喪失了什麼?如果有所喪失,那是每天都在進行的流失──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看得到的具體流失。用抽象語言來說:部落/部族在歸順(服從日本、接受統治)之後,不只喪失政治權,同時也喪失文化權和教養子女的教育權,部落社會並且還承受前所未有的階層化過程;事件之後,起事族人在歷史上失語,徹底喪失話語權。這是一種結構性的大變動。我認為,二二八之後,台灣社會所面臨的也是如此。
今天我們該如何「理解」二二八之後的台灣社會?事件後不久,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帶來了一群為數眾多的人群,光是人口本身就是很大的衝擊,但對島嶼的衝擊,更在於:這發生在二二八之後,也就是當這個島嶼剛經過軍警肅清、血洗,大批領導者、青年、學生和市民死亡,人們嚇破膽,不敢反抗的時候。二二八是禁忌,在地人不能談;新來者對此無知,如果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共產黨+台獨),不只不會給予任何同情,更要加入譴責行列了。不只是二二八這個事件,他們所追隨的政府在教育上、社教上把台灣人的歷史給徹底切除掉。一邊被迫噤聲,一邊完全無知。
外來人群在別人有過去、有創傷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打造出一個全新的生態環境(habitat)。讓我們試著想像:你是追隨黨政軍來台的平民,你住進一個社群,你對在地人的巨大創傷毫無了解(你也有你的悲慘遭遇,但那是可以大談特談的;六十年後你的子女還可以大江大海地談),你不用學他們的語言,不用知道他們的過去,卻可以用仇日的眼光厭惡、指責他們的「日本性」;然後,他們的子女和你的子女在學校學習中華民族的歷史、講國語、學習寫反攻大陸的作文。這一切在新來者的你,都是這麼理所當然。但是,讓我們換個立場想像:你是在地青年,看著大量本地菁英突然消失,甚至看過他們被公然槍斃,而你因為躲到山區才逃過一劫,然後,在心還淌血的時候,你被迫徹底沈默,你的子女在學校被教導一套和這個島嶼完全脫鉤的歷史,他們不要跟你講「低俗的」母語,他們每上一天學,就離鄉土更遠一步,就離島嶼更遠一步,直到完全和你疏離。這一切對你的子女來說,也都這麼理所當然。
新來者對本地歷史和創傷徹底無知,不是他們的過錯,但無形中幫助了獨裁者對在地人的壓迫,卻是事實。以中華民國為名的這個黨國,更將島嶼打造成因戰敗而失去的國土的縮影!全中國城市沒有比台北市更中國,瞧,這裡是杭州南街,這是迪化街,這是潮州街,這裡又是長春街!在這同時,在地人的記憶就被抹消、置換了。獨裁者蔣介石從陽台一望,就是祝福他長年百壽的「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全台灣以「中正」命名的道路更是數不完,他的銅像到處立。中文說這是「為生人立祠」──在一個人活著的時候,拜他如拜神一樣。在肅清過的土地,中國國民黨將這個島嶼黨國化、強人神格化。一位出生於一九一七年的老前輩,感嘆說:日本天皇都沒比蔣介石更像神。這些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是清理過的殺戮之地,並且以可以再度殺戮的黨國軍警暴力為後盾。
我有時會想:本地人的父母,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每天看著子女背書包出門、進門,讀的東西、講的話語(形式和內容),那麼天龍,遙不可及,不知作何感想?看著蕃童教育所的孩童高聲唸アイウエオ,莫那魯道是否也有過同樣的心情?當然,被嚇破膽的人群,大致有兩種選擇:一、自我疏離;二、積極加入。我想起,我的父親,雖然是國小老師,卻從不管我們的功課,但是,我隔壁的鄰居,媽媽跟著小孩讀ㄅㄆㄇㄈ。當時幼小的我還很羨慕,現在回頭看,是很具有揭示性的對比。
不管外省人或台灣人的子弟,我們都是在二二八的三月屠殺後,在大地的鮮血已然清洗,一起接受黨國教育,完全一樣的教育,二二八是禁忌,很少人聽過,就算聽過,也幾乎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更遑論前因後果了。換句話說,我們對距離出生不久前的台灣徹底無知,我們的無知和父母、祖父母輩的知,同時存在,卻是沒有接點的平行線,一顯一晦。複雜的是,這不是純粹的知與不知的問題,它牽涉到現實的利益和權力,於是平行線隱晦的那一邊,不斷有人離開,加入到黨國這邊,老中青少幼,摶成牢不可破的龐大力量。這是何以到現在還是有人不相信二二八真實發生過的深層原因──如果四十年來你都沒聽過,而且腦子塞滿黨國教育的東西,當然很難接受「突然出現」的事件,更不要說ROC軍隊屠殺平民這回事了。也就是在這種結構性的認知體系中,我們看到鄭南榕的突破性貢獻和意義。
眾所周知,鄭南榕被歸為「外省人」,其實他的父親是日治末期來台灣的福州人,他的母親是基隆人。在黨國的省籍分類和父系思維下,他成為「外省人」。我沒有他的傳記資料,我無從得知他童年和成長階段對二二八的認識為何,二二八發生時,他的家人在本地人保護下才得平安度過,但這種情況不限於他那一家,有類似經驗者大都只孤立地講本地人的善心好意,不去碰觸事件本身;如同一些保護過外省人的台灣人,也常孤立地提及這樣的事情,有的表功,有的作為族群融合的見證。鄭南榕顯然沒有將這樣的家庭際遇抽離出來,當成家族史由厄轉安的一樁軼事。他在第一次求職履歷表上就寫道:「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件事帶給我終生的困擾。」他死前親筆簽名的簡歷開宗明義說:「鄭南榕,原籍福建林森,一九四七年生於台灣台北二二八事件的恐怖屠殺後。」他在這一年九月十二日出生,該年有多少人出生?何以一定要寫出生於二二八之年?而且是「恐佈屠殺」之後?他將自己的出生年和二二八連結在一起,早在戒嚴時期就開始。放在當時的時代,實在非常難得,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應該很罕見。究實而言,那是一種宣示,明確宣示他認同台灣,並承擔她的苦難。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鄭南榕超越時代、超越家族、超越族群的眼界和高度。
世界上任何再嚴密的獨裁專制統治,總會有罅縫。關於鄭南榕和其他有志之士在戒嚴時期於 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 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展開平反二二八事件的行動;解嚴後,一群一九四七年出生的人士在一九九一年組織「四七社」,以二二八英靈再生自負自期(鄭南榕想必與之精神同在),這些無庸我在這裡講。我想談的是罅縫問題。通常罅縫只是罅縫,有人透過小小的裂隙,偷看被蒙蔽的世界,鄭南榕和他的同志,不滿意罅縫只是罅縫,他/他們要把它弄得更大,直到它完全破開,顯露那被蒙蔽的整個所在。在禁錮的時代,鄭南榕勇於衝撞,那還不只是勇氣的問題,那是作為行動思想家的鄭南榕給我們的贈禮──他為我們高高樹起自由、民主、獨立、自主的標竿。套用他的話:再來就是我們的事了(Koh-lâi,tio̍h-sī lán ê tāi-chì)。
知道網羅是一回事,以生命衝決網羅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用在這裡提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直到今天都令我們動容的自焚,但是我想在這裡特地談鄭南榕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他所說所言非常清楚,一點都不含糊。他留給世人印象最深的一幕,可能是他在金華國中「反國安法」的演講中,用台語說:「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隨即露出典型的鄭南榕笑容,群眾眾口一聲握拳伸肘重複齊呼:「獨立!獨立!……」。(1987年4月18日;影片收在紀錄片《牽阮的手》)他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他主張台灣獨立,都毫不含糊。在這個魚目混珠、以虛情假意包裝謊言的年代,他的清楚、不含糊格外顯得珍貴。但是在我們賞識他的清楚不含糊之際,我們更要深深警惕到:台灣社會對「含混性」的超高接受度。當「和平」意指「投降」;當主政者一面開山海關一面說這只是和清兵和平交流,很多人毫不懷疑、毫無批判地相信。這在在提醒我們不能輕估戰後國民黨數十年黨國教育的影響,以及舊勢力的盤根錯節、龐大頑強和複製能力。
黨國教育的深層影響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時間框架內的內容,是掌握情境最要注意的。據說,一般動物的幼兒對餵養牠的人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賴和依賴感,因此對預定要放回大自然的動物,一般不會讓牠看到餵養者,即使給飼料的手也要有所僞裝。黨國教育養大的世代絕大多數人對黨國顯然也有一種很深的信賴和依賴感,這也可以解釋何以不少人曾加入政治抗爭運動,黨國再起後,又歸隊了。此刻,台灣社會有解嚴之後成長的年輕世代,也有參與八○、九○年代社會運動的青壯年層,而目前掌握決定未來台灣走向的群體,又是黨國教育影響最深的世代,他們正將台灣帶向一個違反民意、出賣台灣整體利益的方向,如果未來幾年我們無法阻擋這個發展,那麼我們將再度鎖入一個更大的黨國,歷史不只將再度重演,也將再度被改寫。
我們目前面臨很多亟待解決的課題。由於個人關注的面向有限,主要著眼在文化和論述方面。這些基本上都深受威權統治和黨國教育的影響,如何解決,需要集思廣益,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到的。在這裡,我試著將這些課題指認出來,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首先是雙重標準的問題。雙重標準是殖民統治常見的社會心理結構,代表殖民母國的或殖民統治者的東西或事物,恆高於在地的、被殖民者的。台灣戰後經歷國民黨的類殖民統治,由於黨國教育是強力的、密集的、長期的,它的效果往往高於比較鬆散的殖民統治。我們常批評媒體或某些人士、團體,說他們雙重標準,但若從他們的邏輯來看,其實很一致──天龍國的種種原本就高於島嶼的一切。再怎麼批評好像都沒用,更棘手的是,被馴化的人會內化這種等階差序的文化觀,不只自我鄙棄,有時還會表現得比「上位者」更激烈。要如何打破這種情況,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其次是政治嚴重被污名化。政治指處理公共事務的多元機制,包括投票與輿論。在獨裁專制體制下,政治是統治集團的專利;但在民主社會,它是眾人之事,公民透過多元機制一起來管理公共事務。如果公民不參與,就是保證將公共事務的決定權交給統治者,讓他們有機會成為獨裁者。在很多民主國家,由於不同的原因,有一定比例的公民是冷漠的,不會去投票,不表示意見,但成熟的市民社會不會污名化政治。反觀台灣,政治被認為是骯髒的,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去政治化論述」非常盛行,年輕人深受影響,若有人說「那是政治」、「我們不要政治」,就可結束話題。其實只要問:「去政治化論述」對誰最有利?就明白問題所在。如何扭轉這個情勢,值得我們思考。如果年輕人不關心公共事務,那真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危機之一。
最後,是反貼標籤的操作。現在台灣社會最流行的標籤之一是「撕裂族群」,中國國民黨常常拿來貼到民進黨,或本土派人士身上。但果真如此嗎?誰真正撕裂族群?中國國民黨從「撤退來台」之後就開始制度性地區隔「本省人」和「外省人」,優惠前者、歧視後者,哪有比制度化的顯著不公不義更撕裂族群?根據學者的研究,一九五○年開始的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大幅度優惠外省籍考生,至少持續十二年。一九五○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台灣省籍錄取七人,外省籍錄取一七九人,占全部錄取名額96%。一九五六年,高普考本省籍錄取人數占25-29歲人口比例0.006%,遠遠低於外省籍錄取人數占同年齡人口比例0.526%;即使加上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本省籍錄取人數占人口比例仍只有0.061%。最受惠於這個制度的是1925-1936出生的外省籍人士。其實,錄取總人數比高普考更多的特種考試(特考)也同樣優惠上述世代的外省籍人士。(駱明慶,〈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與特種考試的省籍篩選效果〉,2003)一九五○年代學校開始取締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的語言政策,嚴重破壞族群之間的感情;一九七○年代相繼取消最受歡迎的布袋戲和歌仔戲電視節目,規定電視台一天只能播一小時台語節目、兩首台語歌等等(管仁健,〈台灣的霸權國語與悲情方言〉,網址見文末),在在加深本省vs.外省的族群問題。制度化的族群、語言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很深遠,往往是結構性,我們還活在這個惡果當中。這 一兩 年來,馬政府的一些作為,更是撕裂族群感情到極點。但是這樣的中國國民黨,還是能將「撕裂族群」的標籤貼到本土派人士身上。此外,戰後中國國民黨將應屬於政府和人民的龐大日產化為黨有,且在威權時代透過各種機制,官方和私人不知囊獲多少不當收入,這樣龐大的不當利益集團,卻能塑造出反貪形象,遮掩真實。我們必得針對這類逆向操作,探討出有效的破解辦法。
以上只是舉其大絡,我們必須面對並想辦法解決的課題非常多,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也是遍布荊棘之路。我們必須不畏艱難,攜手前進──為了我們的山河,為了我們的年輕人(可幸的是,他們已無本省外省之分了),也為了我們的歷史。
沒有主體,就沒有歷史。如果我們無法捍衛好不容易奮鬥而來的自由、民主、人權,以及多元價值觀,那麼,我們也將喪失歷史的話語權。這一、二十年來,我們透過不斷的探索和思考,逐漸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書寫;因為思想自由,所以研究得以深化,因為觀點多元,所以內容豐富多樣。如果我們鎖入中國,我們的歷史一定會再度被改寫;島嶼的兒女讀的,不再是我們的歷史,不再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歷史。 葉菊蘭 女士懇切請求我們「不要遺忘」,只要台灣還是台灣,鄭南榕不會被遺忘,只會更加被記憶;三十二歲的詹益樺,也是如此。為了他們,為了我們的歷史,我們必須持續奮鬥,直到島嶼的名字就是台灣。
文中所引管仁健,〈台灣的霸權國語與悲情方言〉,網址如下: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814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3/06/07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