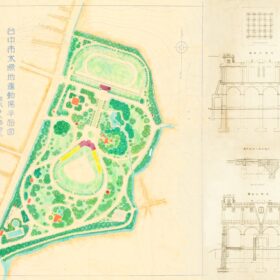我(彩雲)的回憶
高彩雲
郭珮君翻譯、周婉窈校註

編按:這是Obing Tado(高山初子、花岡初子、中山初子、高彩雲)的口述回憶,收在ピホ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實編譯,《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東京:教文館,1988),頁240-244。為了讓此份文獻能廣為國人參考,版主特地商請臺大歷史系碩士生郭珮君同學翻譯成中文。本部落格曾刊出高彩雲口述、高永清紀錄、潘美信譯,〈訣別的悲劇〉,讀者若比對兩份記錄,將會發現其間有落差,孰是孰誤,又是高難度的考證工作,可能永遠是個謎。(周婉窈 2011/11/25)
—————
昭和五年(按,1930) 十月二十六日 ,一郎和花子帶著他們所負責指導的坡阿崙蕃童教育所兒童參加霧社的聯合學藝會,因為還要參加隔天的聯合運動會,一郎夫婦兩人與長男輝男[1]三人在我的宿舍過夜。雖然還是像平常一樣的開朗,但總覺得看起來似乎有些憂鬱。
隔天早晨,一郎、二郎兩人說要參加早晨的練習,一大早就前往武德殿。
回來後,吃了早餐,兩人就各自到自己的職場工作(出勤),也就是,一郎陪著班上的學生去公學校運動場,二郎則是前往分室的電話室。
我和一郎的妻子花子前往公學校的運動場,花子抱著滿月的長男輝男,我則帶著四個便當出門。
到了分室和公學校中間附近的練兵場時(八點前),才看見手持槍枝、竹槍、蕃刀等各式兇器的同胞,就看到他們在殺日本人,心想這可不是小事,就慌張地急忙跑向運動場。和花子走散時,我丟掉便當,和許多日本婦女、小孩一起逃進新原校長[2]先生的宿舍。
攀爬走廊的欄杆打算進到宿舍裡面避難,卻因為被後面的逃難者拉扯下來而好幾次跌落地面。總算爬上去後,因為槍擊而陸續有日本人倒下。外頭傳來了尋找我的聲音:「Tado Nokan的女兒在這裡嗎?是不是被誤射了?」
向著室內的槍擊越來越厲害,所以大家都往廚房逃跑。但是槍擊卻依然激烈,屍體變得越來越多。
我突然被壓在屍體底下,感受到〔屍體的〕重量,這時,歹徒從牆壁的孔穴中將槍口向內瞄準正坐著的日高公醫,砰地一聲,日高公醫[3]的臉被子彈打得面目全非。此時,日高 太太在旁哭喊著「夫君、夫君」(アナタアナタ)。另外,還聽到在走廊咚咚地斬首的聲音。這時,微微聽見外面傳來伯母「Obing,Obing(我的別名)」呼喚我的聲音。我一一推開壓在身上的屍體,悄悄走到外頭。槍聲已經遠去,到處都是屍體。
遇到伯母,才聽說包括父親的六社的同胞起來採取抗日的行動。知道丈夫二郎在家等我,就急忙趕回家裡。一到家,丈夫二郎正用筆在牆壁上寫著遺書。一郎夫婦就站在旁邊,母親也在。聽了細節,才知道整個事情,也感受到前途的黯淡。之後,大家就整理行李一同回到故鄉荷歌社。霧社也已不是昨日的霧社,已經完全不同了。回到故鄉荷歌社,就連那裡也都不再是過去歡樂的部落,周遭都是殺氣。母親帶著弟弟妹妹前往巴蘭社的伯父家避難。我們討論的結果,雖然暫時待在這裡,但決定還是應該離開這裡到山(花岡山)上避難。在山中過了一夜,連一個男人也都沒看到。也不讓我們知道是不是去迎擊了。
到了二十八日下午,花岡一郎和二郎一起回來。二十八日晚上大家一起在山林裡過夜。二十九日早上大家一起討論自殺的事,決定這樣做,於是各自製作麻繩。到了二十九日下午,大家都在脖子上套上麻繩各自靠在樹枝上。這時伯母[4]Iwan Nokan(花子的母親,我的姑姑)像是突然想起來一樣,開始唱起了赴死之歌。這時,巴蘭社的姊夫Walis Tiwas突然出現,制止了我們,他說:「大家不必死,石川部長(石川源六)[5]躲在我的部落裡,還有很多荷歌社的人來避難。」想把我們叫過去。沒辦法,只好又解開了上吊的繩子,下到樹下。
二十九日夜晚快來臨時,Walis走在前頭,我們共數十人跟在後面,打算從花岡山山頂向著濁水溪岸巴蘭社的方向走去。一郎像是突然想起一般,說出了放棄的話。他說:「這樣投降也不是長久之計,與其痛苦死去,還不如果敢地死去。」又表現出想要回頭的意願,就真的回去了山裡。二郎對我說:「你是有身孕的人,說不定能夠得救,就交給命運吧。」完全不打算帶我回到山裡。
(註:這一瞬間就是和丈夫別離的瞬間。我們目送著對方,他看著我的背影,身影慢慢消失在山的陰暗處。我也以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心情沿著溪邊走,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繼續活著,跟在姊夫後面,不知不覺就和伯母Obing Nokan(父親的姊姊,過去是近藤的〔離婚〕妻子)一起到達了巴蘭社。)
就這樣跟著Walis Tiwas,和伯母Obing Nokan一起到了巴蘭社避難,母親和弟弟妹妹也都在那裡。
(註:Walis Tiwas是伯母Iwan Nokan(父親的姊姊)長女Uma Nawi的丈夫,在昭和六年十月十五日清流的歸順日那天被警察逮捕後,就一直沒有回來。)
不久後,我在討伐隊組織的醫療班中協助護士工作,但因為環境不合,在正月左右前往羅多夫的收容所,在那裡和三百人左右的投降者一同生活。
昭和六年五月〔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承蒙好意〕我到駐在所那裏洗澡,那時,那裡的主任安達囑托[6]堅持要我在駐在所過夜。我推辭了他的好意而回家,意外發現了日本警官正在計劃第二霧社事件。好像是同情我吧。[7]四月二十五日早晨,道澤〔社〕壯丁約150人帶著槍枝,一大早就攻擊我們的部落,大多數人都被殺死。我九死一生得以逃出,到達霧社。不論誰都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8]
那年的五月六日早晨,從霧社出發,強制移住到川中島。道路兩旁每十幾公尺就有一位佩劍的警察在戒備。似乎是要防止我們逃跑。昭和六年五月六日的一大早,我們被強制移〔住〕到川中島。約五十公里 左右的路程,傍晚下起雨來,到達川中島是下午五點左右。事出太過突然,當地的農民好像也被要求強制離開。急急忙忙收拾需要的行李,邊回頭張望,留下了約四十甲步[9]的水田,就這樣離開了。糧倉中還留下堆積如山的尚未脫穀的米,這些糧食按人口比例分配,讓我過了半年的生活。
五月十二日生下初男[10]。昭和六年我一個人生活養育遺腹子,昭和七年元旦和高永清結婚。
大概是因為精神疲勞的原因吧,無法分泌母乳,只好靠人工營養辛苦的養育孩子。
亡父(Tado Nokan)[11] 五十三週年( 十一月二日 )
彩雲述 永清記
[1]日文文獻或作「幸雄」。
[2]霧社公學校校長新原重志,他和長男(11歲)、長女(6歲)都死於事發當日。
[3]應該是公醫志柿源次郎。
[4]日本人稱呼伯母、叔母、姑姑、阿姨一概為「おばさん」,漢字寫成「伯母」。這篇口述是用日文寫成,讀者也是日本人,所以寫成「伯母」,但在括弧內說明是父親的姊姊,中文親屬稱謂為「姑姑」。
[5]部長指巡查部長。此時的日本警察人員位階由高至低依序為:警部、警部補、巡查(分為︰部長、甲種、乙種)、警手。
[6]安達健治。
[7]指安達健治囑託一定要她留下來過夜一事,免得她被殺死。
[8]應指日本人對六社遺族被道澤社壯丁襲擊屠殺一事,顯示理所當然(或罪該應得)的表情。
[9]甲步,同甲,面積單位。
[10]即花岡二郎遺腹子Awi Dakis,戰後改名高光華。
[11]荷歌社頭目,死於土魯灣戰役。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12/06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