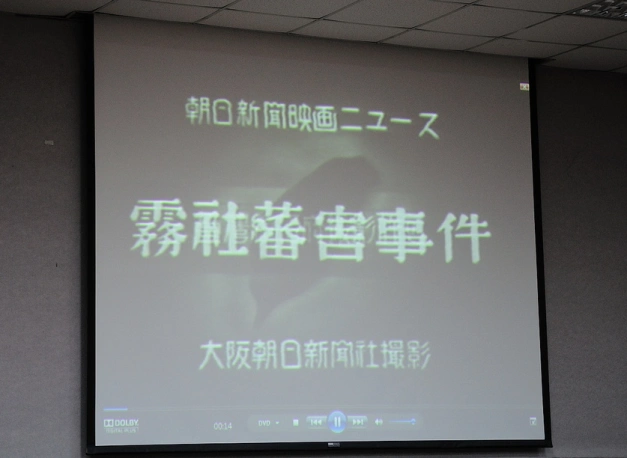「川中島.清流部落的記憶——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記錄
下半場(3)
周馥儀、陳育麒、陳慧先整理,周婉窈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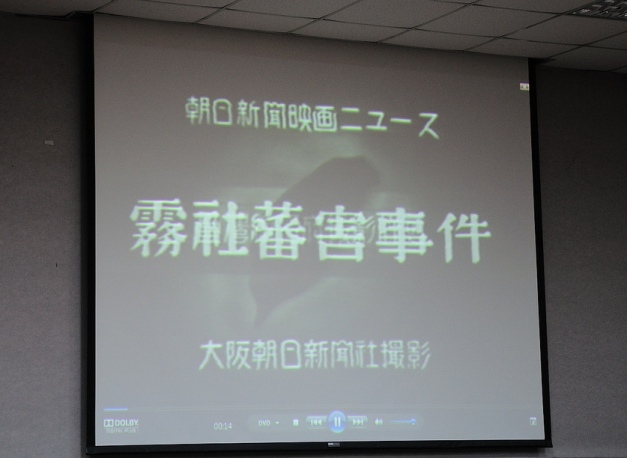
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
我覺得在日據時代發生霧社事件,霧社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人一定會要找到元兇、戰犯,這些壞人,所謂的兇蕃啦。國民政府以後,那些兇蕃是完全轉換為英雄,我覺得不太一致。當時日本所記載的,跟我們國民政府的時候,因為語言不通、轉換過來的這個好像不太一致。
在國民政府以後,我們大概有好幾次戒嚴,很多老人家還在的時候,你們不太可能到我們部落去,尤其是外國人、日本人。我們的族人都只會講日文,大家受日本教育,中華民國實在是不可能讓你們進到我們部落來,除非你有特別的管道,你才可以到。我們有檢查哨,戒嚴時期,我們部落好像是臺灣的一國兩治,我們是國中國,你們進來要申請入山證,尤其是前面二十年,對外面的言論大概是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上,所以你想去了解事實不太可能。我不曉得日據時代那些資料,他們調查的資料是不是完全轉換成中文,轉換成中文以後,很多都不太正確。我在大二的時候曾經寫信給《中央日報》,我說花岡一郎、二郎不是兄弟喔,不是莫那魯道的孩子喔,答覆下來是「文獻會決定了不能更改」。(眾笑)其實現在開始,大家都很幸福,有很大的落差,演戲也好,現在《賽德克‧巴萊》可能馬上要出來了。大家看過軍方的那個影片的話,應該是〔戴〕鋼盔(按,即正規軍人),我看了那個國片,它還是用〔戴〕警察的帽子〔的人〕跟我們在打仗,事實上跟事實差很多,所以還是需要各位歷史系的學生去研究一下。
周婉窈教授:
謝謝Takun先生,那我們是不是請……。
Kuras Tanah古拉斯.達那哈先生:
莫那魯道是英雄,真的在史冊,國民政府認為他是抗日英雄。但是在戒嚴那一段時間,我剛好也回去屏東,黨外運動的那個時代、那個奇怪的時候,他被認為是本土的,那時候沒有叫原住民,本土的類似臺灣人抵抗異族統治跟外來政權,他當時也被冠了這樣一個名詞,那麼從我們Truku,Toda來看莫那魯道,他是不是英雄?我個人認為,在我們族群裡面,他其實是原住民的一個領導者,我肯定他是英雄,我肯定他是英雄。那如果你用原住民,用我們上面那兩個語群Truku跟Toda,他們也許不承認他是英雄,至少,不管你感受好不好、爽不爽這個莫那魯道,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就是,它叫Sediq Balay,Sediq Balay這個翻譯很好。當時我們鄉公所出版霧社事件那一本漫畫書,包括鄧相揚的兩本書,邱若龍要我寫一個序,當時因為還沒有賽德克族,賽德克族是最近前兩三年,2007吧,11月23號才正名。
周婉窈教授:
2008吧。
Kuras Tanah古拉斯.達那哈先生:
2008後才正名。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叫泛泰雅族,在那個序文裡面,我不曉得那本書有沒有在裡面(按,指主持人帶來的書),我就寫了幾句話。我說,霧社事件應該不只是我們賽德克族──泰雅族的一個令人尊敬、值得大家尊敬的事件,我沒有提到莫那魯道,始終我就是對準我們賽德克族,因為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在那個時候,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是對於這個族群,我們絕對肯定。賽德克族,現在已經從泰雅族這邊分離,分了三個出去,當時我就寫了這個序文。
那麼我也跟各位報告,剛剛Tado大哥剛才也講說,霧社事件,如果有英雄是莫那魯道的話,當時荷歌(現在的春陽)部落Tado Nokan,就是他的親祖父,這個人是響叮噹的人物,我們あにき(Aniki,大哥)好像是有一點委屈也好、抱怨也好,每一次霧社事件〔紀念〕的時候被提到的,都是莫那魯道的遺族或者家族,像官方單位,每一次要辦這個祭典的時候,都是以莫那魯道的家族為主,這個〔Tado Nokan〕確實是被忽略到。所以,當時民國65年,我們在重建霧社事件紀念碑時,它前面有那個英雄,有那個烈士啦,我們當時為了這個,跟我們縣府的官員、鄉公所跟文史工作者鄧相揚、邱若龍,談了很久,到底這個英雄碑要不要把莫那魯道的名字寫上去?最後談論的結果,我們認為,打霧社事件這一場〔戰役〕不是只有莫那魯道,他固然是當時的頭目,但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這一點我也跟あにき(大哥)報告,我們覺得,現在在霧社紀念碑裡面的還不只這一些,可能還有一些遺體都沒有帶回來,只有象徵性的埋在那個地方。我們當時也很小心,並沒有把那一個英雄的銅像,把它冠為「莫那魯道」這個名字,這一點我想跟大哥說明一下,也讓各位了解。我覺得莫那魯道是不是英雄,翻成我們賽德克族的話是「Sediq Balay」,是「真正的人」,這個涵義很深,以上簡單來解釋。
另外,剛才宋老師提到正名(按,指恢復族名)的這個部分,賽德克族群回復正名的不到百分之三十,這大概是什麼時候的資料?最近七月嗎?我們原民會的資料好像七千多人。這個七千多人,仁愛鄉有一萬五六千人,扣除泰雅族、布農族跟漢人閩客,還有外省族群的話,七千多人這個比例相當高,可見得這三個語群都相當認同。另外在花蓮三個山地鄉,萬榮鄉、秀林鄉跟卓溪鄉,認同我們這個賽德克族群的,幾乎都是在這三個鄉鎮的領導階層,不是鄉長就是當過校長,教育界蠻多的。他們有一個花蓮縣賽德克族文史傳承協會,他們給我們當時的預估資料至少超過三千人,相當可觀。所以我們原民會預估,大概賽德克族應該可以在一萬兩千人左右,這樣一個數字,當然我們要看戶政的實際認同登記,〔按〕法定的登記族群為主來評定,這邊我作個回應,請參考一下,謝謝。
Umin Sapu桂進德先生:
像我,我認同,也還沒去登記,始終沒有時間去登記。(眾笑)
周婉窈教授:
在座的來賓,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們還有時間。好,請。
來賓(男)提問:
你們賽德克族人為什麼以前長輩不喜歡講霧社事件?是不是有類似白色恐怖這種陰影存在呢?

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
這個我必須講,當然,第一個,是他們傷心的歷史,因為我們清流部落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家庭都有那個傷心的、悲傷的歷史,大家就好像忍辱吞聲,像Tado他只有祖母回來,那有的是只有……大概也不能提到那麼多。重新談過去,一談過去的話要談很多,好像你讓他們再一次回憶他們剛剛死去的人,當然他們不太願意談過去的歷史。再過來,〔霧社事件〕之後,我們5月6號遷過去以後,到10月15號之前,幾乎半年的時間,日本人秘密的慢慢調查,投其所好,給你喝酒、給你東西,「喔,你的孩子這麼壯喔,可能有殺不少日本人、很勇猛。」調查以後,10月15號以後拿到埔里去活埋。所以我們小時候,我隔壁鄰居的阿嬤,〔聽到〕我們講霧社事件,她〔們〕都會罵人,因為她們的先生被抓走了,她們老人家不太願意講。國民政府來以後又都很兇,都是警察軍人,跟日本人差不了多少,都長得很像,(眾笑)都是戴軍帽嘛,(眾笑)以前的警察都很兇,戒嚴時期,講霧社事件一定都會被抓。
Kuras Tanah古拉斯.達那哈先生:
我要從日本人進來以後這一段歷史,看待我們大家〔為什麼〕都不願意談這個事情。Tgdaya不用講,Tgdaya幾乎是滅族,但是我們Truku跟Toda,受到日本人進來以後的高壓統治,事實上也沒有少於Tgdaya族,除了人止關事件[1]──大概是唯一贏過的一場戰爭,霧社番下來打人止關事件。後來像霧社討伐事件,打了兩三次,包括隘勇線前進的時候,設一些關卡之類的。另外就是在1897年深堀大尉他們進來的時候,依我們了解,一半是泰雅族人殺的,一半是我們Truku族人殺的。[2]
有一個Kuras(和我的名字一樣)也告訴我,他說一部分是泰雅族殺的,清境農場彎過去就是泰雅族,這個歷史有歷史文獻,這邊如果有什麼錯誤修正一下沒有關係。我剛才講的意思是,仁愛鄉就現有的行政區域,有泰雅族、有布農族,這裡面很多事件,不是只有賽德克族殺過,包括泰雅族,Slamaw(薩拉茅)事件[3]這個也是嘛,對不對?所以一開始日本人哪裡喜歡Truku?他不喜歡啊,深堀〔安一郎〕大尉進去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古拉斯‧布浪(Kuras Buran)是當時的頭目,不是,Basaw Buran(巴索‧布浪)是當時的頭目,古拉斯‧布浪,聽說他的兄弟,好像是我的曾曾祖父,所以我叫作Kuras(古拉斯),我爸爸取這個名字就是這個原因,紀念我們的老人家。所以Toda也一樣,包括那個第二次所謂的霧社事件,還有姊妹原事件,包括到最後1942年,快要光復的時候,前兩、三年的黃肉溪事件。像這些歷史我想你們從文獻資料裡面都可以找到。
這大概都是我這二十年來聽的一個狀況是,霧社事件當然是最重要,死得很慘。這五十年來,其實我們仁愛鄉現有這個行政區域裡面,它肅殺的那種氣氛,確實相當恐怖,包括最後,所謂徵兵到南洋去打仗,我伯父是這樣去就一去不回了。有很多的狀況,我覺得是整個氛圍、整個氣氛讓原住民,就現有的這些幾個族群,不是只有賽德克族群,覺得要活在當下,日本人的統治這一段時間,大家都不願意談。是不是二二八事件有影響?我不太清楚,但是,基本上日本人統治五十年來,幾乎就是武力鎮壓,所以他要分生蕃、北蕃。我聽他們老人家講,對付生蕃,是帶出去,「臨時處決」……那個就是槍斃,帶出去就斃啦。但是對所謂的南蕃,排灣族、魯凱族他們,他是用比較和緩的手段。仁愛鄉這個部分也是一樣,它也有所謂的南蕃跟北蕃,北蕃也就是生蕃,處理的方式就是不審、帶出去就斃了。幾十年來,是這樣對待原住民。當然大家都不願意談這個事情,怕有所誅連……種種原因,一直到光復之前,還有所謂的黃肉溪事件。講白了就是類似像白色恐怖,沒有辦法讓人家接受,所以正面來談〔霧社事件〕這個事情,大概是這最近二十年大家才願意談。這是我的回應,謝謝。
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
這個……我順便講一下,1990年到1992年之間,我去訪問我的老人家,他非常熟悉我,有的是我部落馬赫坡部落的長輩。我去問他,我不是去問霧社事件,那時候我最初,主要是要去重新學習我的歷史文化。不過你一談到家譜,他就開始講霧社事件,他講到霧社事件的時候,他避重就輕。好吧,他一提我就問,我一問的時候,他就會問我:「Dakis,這個可以講了嗎?」你看看,他的那種……。我簡單講我的祖父,日本人走了,這個國民黨、國民政府又來了,我的祖父認為是一樣的,所以他還是不能講,怕等下就不見了。他是這樣子的感覺,因為我們事件以來一直這樣,最後一次就是我們到那邊找屍體,10月15號又去收一次,所以那個真的是很恐怖、很恐怖的。因為我要對照、我要對證,老人家還會問我、還看著我說:「可以講了嗎?」光這一句,你看看,所以很多故事都被我們的老人家帶走了,很可惜。
來賓(男)提問:
講霧社事件講太多,日本人可能會以為你有參加那霧社事件。(眾笑)日本人一直在找這個兇手。還有你們遷居到川中島的時候,因為男人大部分都戰死了,是不是剩下婦女跟小孩比較多?

Tado Nawi高信昭先生:
這個我作簡單的報告,我們剛迫遷到川中島,很坦白講,沒有一個家庭的成員是完整的,〔如果家裡還〕有壯年(按,青壯年)的,日本警察還是會蒐集、慢慢的把名單湊出來,假藉名義,帶到埔里去,帶了一百零六個人。我特別問老人家那時候〔的情形〕……黃阿笑的媽媽還在,他們剛好有去。去了以後,中午本來要吃飯,他(按,日本警察)把抓去的那年輕人衣服,全部丟到他們面前,他們〔知道〕完了,年輕人都沒有了。結果他們就走路回部落,〔回到部落〕就跟〔其他人〕講說「我們的壯年(青壯年)都沒有了」。所以那一段時間是只有媽媽跟小孩子,所以那一段時間我們非常感謝眉原部落的人,〔他們〕供給我們種子還有糧食,這個是我們做子女、後代的,一直到現在一直感念、一直感謝他們的。這樣簡單報告,以上。
[1]人止關事件,發生於1902年4月。霧社群(Tgdaya)以傳統武器和戰術,並利用地形、地物,成功阻擋日軍埔里守備隊進入霧社地區。人止關位於臺十四線(舊埔霧公路段),距離霧社約二至三公里的山腳下,是進處霧社地區的隘口,當年隘口峽谷兩側峭壁上方的山腹和緩坡地,散住著霧社群的多岸(Tongan),西寶(Sipo)、巴蘭(Paran)三個部落。以此,人止關之役以這三個部落的族人為主,馬赫坡社由於地理位置更為裡面,無法前往支援。(見Dakis Pawan郭明正,《真相‧巴萊》書稿)
[2]指深堀大尉事件。1897年1月下旬日日本人深堀安一郎大尉率領名為「中央橫斷隊」的探險隊,抵達埔里,擬經由霧社山區橫越中央山脈主脊能高山到花蓮港廳。深堀大尉一行十四人,於2月8日抵達天池,於此紮營過夜。當夜一行人為被迫隨行的Sado社壯丁所殺。Sado社屬於賽德克族Truku(德路固)語群。此一事件之後,日本官方實施「生計大封鎖」,嚴禁食鹽、鐵器等生計用品進入霧社山區。這也是1903年姊妹原事件的前因。
[3]薩拉矛件,發生在1920年。該年7月,霧社當局出動警備員征討薩拉矛番(群),以莫那魯道為首的霧社群以及德路固各社頭目、有力人士,謀議趁其空虛,襲擊霧社地方警備線,大殺日本人。警方獲知消息之後,考量尚無力嚴加懲處,為轉移目標,遂將疑似關係者約四十名,編成蕃人奇襲隊,參與薩拉矛群的討伐,結果導致烏來路馬社頭目以下二十名被獵首。參見戴國煇編著、魏廷朝翻譯,《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臺北:國史館,2002),頁502。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09/24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