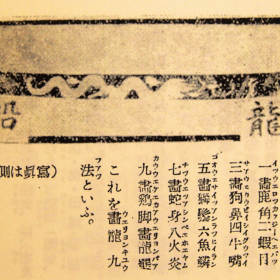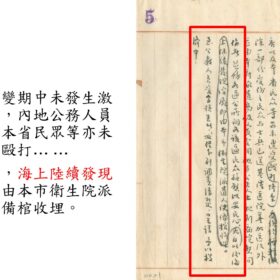「川中島.清流部落的記憶——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記錄
下半場(2)
周馥儀、陳育麒、陳慧先整理,周婉窈校注

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
《風中緋櫻》拍的時候,事實上我是覺得蠻可惜的,第一個是,我們的祖父輩,一直到我媽媽、到我們這一輩,在部落裡面幾乎是不談霧社事件,這是很大的原因,所以我們不了解。到我們,像我自己到大學才知道什麼叫霧社事件,所以這也有它的原因,變成我們對自己的歷史不了解,不是不了解,而是不能講,這是影響之一,所以霧社事件,對年輕人來講「這好像不是我們的事情」。第二個,它的內容我們不是很滿意,因為它的內容,主角應該是他的姑媽Obing,Tado的姑媽Obing,Obing怎麼會跟那個Pihu[1]在那邊,飄媚眼、談戀愛?(眾笑)不太可能。事實上,Pihu對我們來講像個浪人,日本人講浪人,是從小就在外面遊蕩。不太可能,我們以前古代,以前的人是很嚴謹的。這個我跟鄧相揚也講過,我說這個好像有點不對,他說:「演戲嘛!應該要有一點……」我們以前哪有自由戀愛的,沒有吧,那是演戲吧。內容我還是不太滿意,希望將來這個符合事實,我前面也講過「歷史符合事實」,取得大家的共認、共識的話,我想這樣會比較好。
對立的問題,當然經過國家機器的操弄,其實,事實上我們賽德克族撕裂感情的這八十年來,之前也沒那麼嚴重,也許各部落會打架,這是個人造成的,年輕人可能會打架,獵場的糾紛也會有,經過霧社事件以後,確實那個內心裡面,雖然說像我的祖父,像我家族應該是有Toda的血統,因為所有的Tgdaya人只有我們家裡有Pukuh〔這樣的名字〕,[2]這個名稱別家是沒有的。但是我的祖父從來沒有講他的親戚是誰,我很懷疑應該是Toda的Tnbarah那邊的,所以他都不講,像我的祖父祖母經過事件、經過悲傷的歷史,他從來沒有說日本不好,也沒有講說Toda就是不好,他們不講……也許他們真的含恨了二十年也不一定,所以不講也不好,對不對?所以現在我們來講,我們還是要講。事實上不要講霧社事件的話,我們三個族非常融合,像Tado,他的太太就是Toda的,他的妹妹也嫁給了Truku的,你說不好嗎?你們不要講霧社事件,他的妹妹嫁給Truku,他的太太本身是Toda,每到10月27號這個時間大概感覺有點敏感,所以應該是沒有那麼嚴重,尤其現在大家同樣是受中華民國教育。
之所以會那麼快融合,我覺得第一個是,霧社事件以後的十幾年,大家又同時當了高砂義勇軍。不管你原來的族群,在南洋作戰,高砂義勇軍就融合,也變成同一陣線;第二個就是教會的力量,因為這個力量所以我們清流幾乎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大概都是Toda、Truku,假如說他們那麼恨我們,應該不會嫁,郭明正的那個嬸嬸,好幾個都是你們的傳人,我們說的Toda,應該不是問題。
所以Mona Rudo(莫那魯道)的定位有問題。事實上Mona Rudo(莫那魯道)在霧社事件之前,就是我們在部落時代的時候,日本人沒有來以前,他是在我們這個Seediq的族群裡面,我們自稱Seediq,一般日本講霧社蕃的,這個傳統領域裡面,守住自己的傳統領域一定會講說他個人過人的那種能力。在我們Seediq族群裡面,荷歌社gungu那裡的頭目他們一樣是英雄,因為過去有固定的獵場,而且日本人沒來以前,我們部落還是跟他一樣也會拿人頭,所以他在武力方面,在我們傳統領域裡面來講,他是非常傳奇的人物,他的功勞是功不可沒,他個人的魅力、威望實在夠;可是我們被統治三十年、二十七年以後才發生霧社事件,在這個事件的所有戰役裡面是沒有Mona Rudo(莫那魯道),所有的戰役〔是〕我們自己,只有日本人講什麼戰役,在裡面還是有Tado Nokan,還有Pukuh Walis跟那個……都有啦。如果講霧社事件的戰役的話,事實上,我們各部落有各部落的頭目,我這個部落不可能去聽你那個部落的頭目,當然大家不太了解我們部落的這個觀點的話,會以為我們有個總指揮,事實上現在一般人反而把莫那魯道變成總指揮了,他們部落裡面可能有人會講話。他過去在我們部落裡面是確實有他的威望,可是發生那麼大的事情,日本也找不到那個主兇是誰、總指揮是誰,〔就認為〕當然是他嘛。事實上他的孩子可能是近因,[3]就是爆發點。所以我自己寫的報告裡面說是長期累積的恩怨,要不然日本是軍國主義,它的情報系統都固定的、非常厲害,是民怨越深。但是我不曉得二二八事件誰是主謀。我認為霧社事件是民怨太深,才發生共同的,只要有一個人一點(燃),就全部站出來,事實上實際參戰的那些人好像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找出來。我們都知道鐮田啊、安達,他們日本人這些人,但是我們自己部落的主角都沒出來。

宋秀環老師:
那請問您,不知您如何看待由Pihu Walis(畢荷瓦利斯)跟Awi Hepah(阿威赫拔哈)所主導的霧社事件論述,那您的看法是?
周婉窈教授:
是不是Dakis先生要回答一下?
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
我不知道回答得好不好,就是大家分享。第一個,我以前當然用,兩本都用日文寫,目前高愛德Awi Hepah(阿威赫拔哈)先生的書有翻譯本,就是《証言霧社事件》,我們 高永清 先生Pihu Walis(畢荷瓦利斯)的書還沒有翻譯。[4]在還沒有翻譯之前,就是日文版的時候,我跟Takun看,雖然我們看不懂,我們盡力看。
以我的感覺,第一個,我先講Awi Hepah(阿威赫拔哈)的部分,我覺得他的角度好像是站在我們族人的立場,不過,他裡面很多漏洞,我講一點就好。他好像每一個戰役都參加,我告訴你,他那時候才十四歲,不會到十五歲吧,他怎麼可能去打仗呢?怎麼他每一個戰役都可以說他在那邊呢?不對。
當然,我過去是絕對尊重長輩、祖先的,他們都是很優秀的兩個人,到清流的時候,是事件之後最優秀的族人。那我要批評,有時候我不太敢,因為他們也算是我的祖父輩。像我祖父那般年齡的長輩那時候很多,等到我二十幾年前(約1991年),再去找那些人的時候,很多都過世了,連我祖父一句都沒有告訴我,他說:「問這些幹嘛?」連Takun的祖父,我也不知道他在霧社事件裡作了什麼事。不過那個時候可以去問他,有唸書唸得好,就他們兩個。基本上他們兩個,他們都沒有參與實戰,我認為他們絕對沒有什麼少年隊跟著打,我真的很懷疑。他們說那個事件的時候有老人隊、青年隊什麼,這個我真的懷疑。第一個,我為什麼懷疑,我們那時候獵槍都收掉了,你要去打獵就要跟派出所借,借的時候,子彈是有限制的,除非你很準,你可以打三隻還有兩顆,還是可以這樣。不然我想他們用槍的機會不大,所以Awi Hepah講每一個戰役他都有參與,我是質疑的。第二點,那……。
宋秀環老師:
關於您所說的這點,根據他在其著作中的敘述,很多事情的得知是經由實際參與這場戰役的親戚朋友中得知。

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
對,應該是那樣。問題是他好像有他加很多……我是看翻譯本,我才有這種感覺。那第二點,好像每一個戰役裡面都是他的親戚,這個我也是非常質疑。
第二個我要講Pihu Walis(畢荷瓦利斯), 高永清 先生,他非常的聰明,因為那個年代……,他也算Tado的姑丈。第一個我要講就是說,他連Pusu Qhuni都沒有去過,我也是聽老人這樣講,沒有去過。所以當日本人問他們Pusu Qhuni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告訴他們那個是指什麼,那是巨大的岩石,我推斷他是唸書的人,所以他可能不會打獵。
第二點,他根本可能沒有好好聽到Pusu Qhuni的故事,他裡面最後寫了中文,那個中文是要看又看不懂,我自己的感覺。他裡面寫了一章很多東西,也是我們老人家告訴他的,尤其是我們Ruru Tbyawan(土布亞灣)戰役,就是Toda的頭目被我們打死的那場戰役,那個是第一個……。我們Awi Tado(曾少聰)講,因為他是在裡面的人,那個人被忽略了。所以我想Tado在講說很多人真的犧牲的沒被講到,都一直集中在某些人,Tado的感覺也是這樣。
所以這兩本書,別人很難去把它批評,只有我們可以。那我要批評我的祖先,我也可能會手軟,我絕對會,因為我很多疑點在裡邊。因為你們不太了解他們的背景,他的族語能力,那時候翻譯人的能力,所以他會寫成那樣。我想,我相信我的子孫絕對會對這兩本書有所反應,我想是這樣,我自己首先會反應,因為我明年就會寫。
那講到這個《風中緋櫻》,我馬上要講到《賽德克‧巴萊》,因為那裡面一樣沒有呈現我們的英雄,一樣呈現Pihu Walis跟Pihu Sapu是英雄,[5]這個我實在是非常無奈,因為我是這部電影的族語指導人員,我不敢講說是老師,我全程參與。很多族人就跟我講為什麼不反應,就是因為前面有《風中緋櫻》,我也問過 相揚 老師,他說歷史跟電影要區隔,是戲劇,但我也很難忍受,那我也偶爾就算了──電影嘛。因為我也成了他們拍電影的成員,會引起很大的討論,不過我會隨著這個電影的各種情節,我會寫一本書,我絕對會寫一本書。他這樣講,我要告訴你,我所聽到的是什麼。我跟導演也已經有默契,他說可以寫。他那個人也可愛啦,也很有衝勁,他這個人是這樣,平常好像你看他笨笨的(眾笑),不過他拍戲的時候,原來導演是這麼大。裡面的內容,我看了,我的族人看了,一樣到時後會罵我,因為我是族語的指導員。以前我們好幾個都是《風中緋櫻》的顧問,我的朋友會看《風中緋櫻》,演了兩次、兩集、兩天了,差不多兩集就開始打電話、開始打電話給我,後來我真的不好意思。我看了一集到兩集,我就沒有看,我的感覺是,因為一個是國語發音,一個是內容,我自己會混亂,我就沒有看。這樣的故事一定要我看,很抱歉我看不下去。對,就是這樣,我的意見就到這裡。
[1]指Pihu Sapu(畢荷沙布),被官方視為「不良蕃丁」,抱持抗官態度。根據日文資料,畢荷沙布是霧社事件的首謀策劃者。1930年10月24日晚上,趁著眾人對霧社小學校寄宿建築材料的搬運問題而慷慨憤慨之際,他和八位同志謀議藉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大殺日本人,於是由畢荷沙布說動莫那魯道等六社頭目。餘生後裔根據族老的傳述,得知畢荷沙布因居無定所,且經常惹是生非,被族人視為「部落浪人」。以此,說他能夠在短期間內說動六社部落頭目起義抗暴,令人懷疑其真實性。(見前引Dakis Pawan郭明正,《真相‧巴萊》書稿)不過,反日的部落浪人,在起義後英勇作戰,誠可歌可泣。畢荷沙布參與荷歌社頭目Tado Nokan(達多諾幹)領導的Truwan(塔羅灣)戰役,和日軍鏖戰多時,日方稱之為「松井高地之役」。Tado Nokan在此戰役中戰死,成為第一位犧牲的頭目。畢荷沙布最後被捕,於1931年12月和其他慘遭「十月清算」的霧社群族人一起被關在能高郡役所的留置場(拘留所),第二年三月初「病死」。其最後的際遇,讓人不忍想像。
[2]據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解釋,「Pukuh」是都達群的名字。
[3]指莫那魯道的大兒子達多莫那、二兒子巴索莫那。
[4]即註2提到的ピホ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実編譯,《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
[5]Pihu Walis(畢荷瓦力斯)是Pihu Sapu(畢荷沙布)的堂兄。畢荷瓦歷斯的父親Walis Robo(瓦力斯洛柏)有抗日言行,又屢犯禁令,全家深夜入眠時遭日本警察槍殺,並焚燒其住屋。畢荷瓦力斯,當時約十歲,因在叔叔家過夜而逃過一劫,但和被驚醒的族人一起目睹自己的家毀於大火。其後畢荷瓦力斯由叔叔收留撫養,自幼仇日、反日,長大後憤世嫉俗,個性孤僻寡言。(見Dakis Pawan郭明正,《真相‧巴萊》書稿)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09/24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