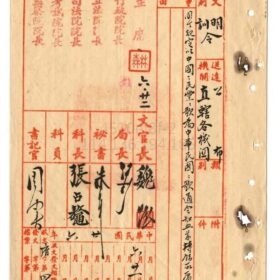「川中島.清流部落的記憶——霧社事件八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記錄
下半場(1)
周馥儀、陳育麒、陳慧先整理,周婉窈校注
與談人:
Tado Nawi(高信昭)先生
Takun Walis(邱建堂)先生
Uya Pawan(洪良全)先生
Kuras Tanah(古拉斯.達那哈)先生
Dakis Pawan(郭明正)先生
Umin Sapu(桂進德)先生
主持人: 周婉窈教授
日期:2010年11月19日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周婉窈教授:
各位來賓,我們時間差不多了,接下來是問答時段,我希望能夠輕鬆一點,雖然這個霧社事件是很嚴肅的事件,但我們心情還是可以輕鬆一點。我希望能夠激發更多的討論,這也是今天引言人的共同希望──希望透過討論,來激發思考。我們現在是不是先請Iwan Pering(伊婉‧貝林)女士? 伊婉 女士和Dakis先生編了《清流生命史》[1],請她先講點話。
Iwan Pering伊婉‧貝林女士:
各位大家好,我叫Iwan Pering(伊婉‧貝林),叫我伊婉就可以了。我的部落是在Alang Tongan(眉溪),其實在霧社事件的時候我的部落沒有參戰,跟巴蘭是一樣的。我想可以有一些參考的資料,在大家的手上就是,好像是在Dakis後面那一篇。[2]我用了部落觀點,從Gaya的角度去探討霧社事件在部落的一些看法。
所以有幾個戰爭的歷史脈絡,其實影響了我們在霧社事件的一些選擇,所以為什麼Tongan(眉溪)跟Paran(巴蘭)沒有參加這個霧社事件,就是因為前面已經發生姊妹原事件[3],其實我們的部落已經死傷很多了。那剛提到有很多婦女的先生去打仗,為什麼她們那麼多人會跟著去上吊?其實從我自己跟老人在提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很多婦女就說,她們就是跟著她們自己的先生走了,因為留下來可能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然後就全部都跟著走,好像也沒有其他的理由,我們就是一起走,一起到祖靈的故鄉。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是可以再從部落的一些想法去討論。我們跟Dakis,還有Takun他們在部落裡面也談蠻多的,我們需要加油。希望有更多比較是從部落觀點出來的東西可以討論,謝謝。

周婉窈教授:
謝謝伊婉女士。我想我們現在就開放提問,任何問題都歡迎。好, 宋 老師。
宋秀環老師:
大家好,我可以坐著講嗎?
周婉窈教授:
可以,但是請用麥克風好不好?我們可能要錄音、整理。
宋秀環老師:
因為我在清流部落做了很多年的田野, 從博士課程到現在近二十年的時間,清流部落對我來講,無比的熟悉。談及霧社事件的史料非常、非常地多,而在部落人─Awi Hepah(阿威赫拔哈)跟Pihu Walis(畢荷瓦利斯)的兩人著作中,[4]依然是傾向於剛才所說的——莫那魯道是英雄的說法。在整個霧社事件裡面,他們成了主要報導人,敘述著霧社事件的故事,並流傳著。關於這一點,不曉得在座的部落菁英們,是如何地看待這兩本著作?又何地看待這兩位同為部落人的作者?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霧社年輕人對霧社事件的漠不關心。《風中緋櫻》這齣連續劇在公視播放時,我人正好在清流,當時我問了許多清流部落的當地年輕人,如何看待這《風中緋櫻》這齣戲?大多數人給我的回答是:沒看、沒時間看、不想看。也就是說,整個部落的年輕人,對霧社事件沒有太大的關心或共鳴。不知在座的菁英們,如何在年輕人不關心、老年人逐漸凋零下,去整合或建構一個你們所討論的:一個大家都能夠認同的霧社事件故事。
我很慶幸的在老年人凋零之前,換句話說,早在二十年前在清流從事田野工作時,拜訪了許多的老人,當時幾乎每位人在清流的六十五歲以上老人都是我的報導人。至於剛才所提及的對立關係,我個人也有所感。在清流之後,我不僅去了Toda的部落,也去了Truku的部落,還有其他的地方,Toda人不喜歡Tgdaya人,是個事實,事實上許多其他霧社周邊的部族也不喜歡Tgdaya人;而Tgdaya人不喜歡Toda人,也是個事實。我清楚的記得Awi在臨終的前一兩年曾多次對我說:「我最近常常做夢,夢見Toda人來殺我。」霧社事件對他而言是揮之不去的夢魘,陰影依舊纏繞著他。而後,我把Awi的夢境告知Toda老人。Toda老人的回覆是:「那真是活該,因為Awi整天在說我們的壞話,做了很多的孽,才會做這樣的夢。」當時我的感觸非常深,心想:如此的對立關係,不曉得要持續到何時?可能要等到這些老人們全部過世吧!
整個過程一直到正名,我們也看到很多菁英,在正名過程中努力奔走,為了不過是族群和諧,進而融合、認同,最後能順利步上正名之途。事實上,在整個過程裡,有許多牧師在幕後默默耕耘,他們所付出的心血不可抹滅許多牧師們付出了相當大的,但也不知是否是因為我沒看到,總覺得沒看到所謂的「和諧」或者說是「融合」或「認同」。不曉得諸位如何看待正名一事?事實上,今年的暑假我也去了鄉公所,鄉公所的人告訴我,來登記正名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以這樣的人數似乎無法說服大眾─霧社已無認同問題。不知在座的部落菁英們,你們是如何看待霧社事件與認同或正名之間的關係?謝謝。

周婉窈教授:
好, 謝謝宋老師的提問。在座的賽德克族來賓,誰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宋秀環老師:
有夠尖銳吧?(眾笑)
Umin Sapu 桂進德先生:
我先講一點點,給晚輩先講。如果說不和諧的話,我們怎麼會通婚或結婚,或一起工作呢?所以「不和諧」這個措詞,可能可以換個名詞。像我自己當校長在仁愛鄉的國小服務二十六年來講,我走過那麼多部落,不是只有在我們Tgdaya部落,我現在是在發生過姊妹原事件的地方服務,是曲冰遺址那兒的萬豐村落,是過去殺我們賽德克族的布農族卓社的後代。我心中無怨也無恨,這是我個人,我們部落裡面很多人也是一樣。這是我個人的感覺,我們多數人、我所接觸的也是一樣,我們不會把前人──不要說惡業,這種不幸的殘忍的共業,帶到我們這一世來,畢竟我們已經是這樣子,這是我們對和不和諧的一個想法。
《風中緋櫻》,我自己有看過電視,也不是看很完整,反而我在埔里街上或臺中街上,平地、閩南漢人朋友家裡面,也發現其他人,包含教育界的老師,他們很喜歡看,晚上一定要看。他們說,我的同學有原住民,他指我和其他的人,他們就很喜歡看。我自己不排斥看,因為我所知道的也不會輸給編劇,我實在很高興有編成這樣一個影劇,我是抱著欣賞的角度,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到部落去問,可能我們問的群體也不是全部,也有我們原住民同胞也在看,甚至,有小孩子會問問題。其次,也不能強求每一個人都一定要看才是認同這個編劇的整個寫法。我們都是抱著欣賞角度,這是我的想法。換Tado Nawi前輩來談。
Tado Nawi 高信昭先生:
那個《風中緋櫻》我也很少看,有一次我到埔里,我去找我嫂嫂潘美信,花岡二郎的媳婦,我去那邊找她。我跟她講:「妳有沒有看這一部影片?」她說:「Tado,我也很少看。」剛剛播了幾集以後,萬仁導演有打電話問她:「你看了有什麼感想?」我嫂嫂就跟他講說:「好像不太滿意。」他說:「因為那個是商業電視臺,我們也沒有辦法好好運作。」因為那個收視率〔的原因〕,他要有很高收視率才有辦法。
宋秀環老師:
那是公視,又沒有廣告。
Tado Nawi高信昭先生:
有,他們有。
周婉窈教授:
那是公視嗎?
宋秀環老師:
那是公視的戲劇。
Tado Nawi高信昭先生:
但是,因為它可能有商業用途,我嫂嫂就講說,須要加入一些情節,她是這樣跟我講的,我實際上看了,好像是幕後有導演在那裡主導。我也很少看,因為跟我們想像的那個真是太遙遠,謝謝。
周婉窈教授:
謝謝Tado先生的回答。
Umin Sapu桂進德先生:
還有登記賽德克族人數少的那個問題。我個人是認同的,我生來就是原住民,賽德克族的,雖然,也是還沒有去登記,遲早會去登記的。我在想,可能是,登不登記,因為沒有急迫性,而且,可能忙或其它因素,沒有急著去登記。我深信,還沒有去登記的多數人,內心應該是像我一樣認同的,可能還沒有很強的誘因或方便等因素,所以,登記的數目好像不大。我也是想:戶政上族籍的登記,應該有什麼方便,或到部落來服務登記的話,那就不一樣了。
[1]簡鴻模、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清流部落生命史》(南投: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同舟協會發行;台北:永望文化出版,2002。)
[2]座談會發給來賓的參考資料之一:伊婉.貝林,「以部落觀點看賽德克族Gaya與霧社事件關連性的初探──以Tgdaya語群的Tongan部落為例」,發表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合辦,「霧社事件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10年10月25-26日。
[3]從受害者角度,此一事件可以稱之為「姊妹原誘殺慘案」。姊妹原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萬豐村東北方約一公里的平野地,屬於布農族干卓萬群的傳統領域。1903年10月5日霧社群一百二十餘名族人抵達該地,預定和布農族換取物質,主要是鹽和狩獵用彈藥。來交換物質的霧社群以巴蘭社為主,近百人,其餘來自西寶、羅多夫、荷歌三社。這是由一位嫁給埔里平埔族的巴蘭社婦女從中牽線,實則這位婦女已被日本警方吸收為線民。霧社群族人被設計卸下獵刀,和布農族人飲酒。就在霧社群族人酩酊之際,遭布農族裡外圍攻,百餘人慘遭殺害,僅三到五人逃脫。死亡者約八成來自巴蘭社,受害慘重。(見Dakis Pawan郭明正,《真相‧巴萊》書稿,即將出版)
[4]指アウイヘッパハ(高愛德)著、許介麟編,《証言霧社事件──台湾山地人の抗日蜂起》(東京:草風館,1985),以及ピホワリス(高永清)著、加藤實編譯,《霧社緋桜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東京:教文館,1988)。前一本書有中譯本,即阿威赫拔哈口述,許介麟編著、林道生翻譯,《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
(文章轉載自:臺灣與海洋亞洲 2011/09/24 網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