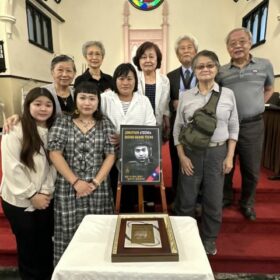六龜高中的同學考上「台大社會系」(成為創校首位上台大的學生),卻被發文嘲笑
張育萌
六龜高中的同學考上「台大社會系」(成為創校首位上台大的學生),卻被發文嘲笑。
華真老師說,社會學是「商品化程度」很低的一種知識。的確。但我可以很堅定地說,是社會學讓我能「把生活當做志業」。我人生最幸運的事之一,就是讀了社會系。
大學時,親戚聽到我考上台大,都會「哇」的讚嘆,接著問「什麼系?希望你表弟以後可以叫你學長欸!」在我彆扭地講出「社會系」之後,三姑六婆經常會短暫地表情管理失敗,眉頭微皺、再快速擠出一個禮貌的微笑,安慰說「也不錯啊!當志工嗎?」「就是那些搞社運的嘛?」
社會學的商品化程度低到,大一大二我在杜鵑花節擺攤(科系博覽會),遇到window shopping的學弟妹,手上拿著管院、經濟系的傳單,狐疑地走向社會系攤位時,我都會用最熱情的語氣、機械化地覆誦「我們社會系的出路很廣哦!可以當記者、老師、公務員,也可以做新媒體、NGO工作」。
「出路很廣」是對學弟妹說,也是在消化自己對未來的茫然。(當時的口頭禪是「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
我上社會系前一年,學生佔領立法院,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政治路徑;隔一年,更年輕的一群高中生為了「黑箱課綱」,遍地開花、各地串連。
我當時覺得世界爛透了,把社會系當第一志願,很多老師都覺得我瘋了,「你要不要再想一下」。有一位我高中的恩師,當時偷偷告訴我,「你讀社會系,我舉雙手雙腳贊成。如果真的逼你讀其他系,你才會真的發瘋」。
( 這位高中老師教我在面試的時候,要提到一本叫《見樹又見林》的社會學聖經——果然,面試當天,我自我介紹完,教授就問我「你最喜歡讀什麼書」。我因為猜題命中,很興奮地搶答「見樹——」大概是因為所有人都制式回答,教授竟然打斷我說「換一本」,現在想起來真的是誠實為上策 )
博班的傳凱學長開啟了我這趟「社會學的奇幻旅程」。大一那年,請激昂而謹慎地請我們思考,「你口渴走進 7-11 ,為什麼下意識拿的是CC LEMON,而不是保力達B?」這是你真實好惡嗎?為什麼你走向櫃檯,拿出銅板、不必說話,店員就預設這是「結帳」的劇本?
社會學經常在這樣「美好的午後」,不合時宜地闖入。
我的社會系摯友Coco(人家現在是月入斗金的工程師,到底誰敢說社會系沒出息),在公共社會學實習課的期末發表,請我坐在教室最後面,等她報告完一起去吃宵夜。我原本打算躲在角落,卻意外聽完了同學們透過社會學眼光展開的種種行動。
有學長姊回到家鄉,成立背包客棧,也用田野調查紀錄農村;也有人用社會組織的視角,延續抗爭組織的動能,成為地方創生、在地青年培力的團隊——有學長說「社會學的眼光讓我把生活作為一種抵抗」,我聽了覺得有夠浪漫。
說時遲那時快,東升老師(我當時的導師)目光突然落在黑暗角落裡的我,問說「你聽了這麼久,有什麼想法?」我腦袋一片空白,支支吾吾地回應「學社會學⋯⋯至少讓我⋯⋯人生不順的時候知道不是自己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的問題⋯⋯」
東升老師微笑反問我,「你怎麼會覺得,你讀了社會學,人生還會有順的時候?」(可惡)他繼續說:社會學讓我們知道,面對一片廢墟,我們可以如何重建。
「重建的過程很漫長,像在跑長程的馬拉松——馬拉松和短跑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起跑的時候看不到終點在哪。」
東升老師說,跑馬拉松的過程,你也許需要停下來喝口水,也可能會遲疑「盡頭到底在哪」。這時,能夠支撐我們的,正是知識跟良知——社會學作為一門「知識」,他可以回答你,「原來在兩百年前,有人跟你有一樣的疑惑。他大膽嘗試過什麼樣的方法,失敗了,我們別重道覆轍。」
嘉苓老師在小畢典上,曾經引用政大熊瑞梅老師的研究。熊老師調查( 2014 年 6 月)發現,「台灣人有七成想對社會有貢獻」,遠遠超過中國、日本和南韓。這個驚人的發現正體現,我們身在秩序繽紛的年代,滿腔熱血,而社會學正給了「豐富的工具箱」。
社會學讓我們懂得批判,瘋起來連自己都罵——大二那年,我夥同社工系的夥伴大肆批判,高舉性別友善的社會社工系館,卻沒有性別友善廁所。
嘉苓老師聽了我義憤填膺地提案,告訴我她親眼看見的故事。她說 2002 年,她跟老師們一起到丹麥。她看著哥本哈根的街頭,好多男人們悠閒地聊天、一邊推著嬰兒車,多數的公民騎腳踏車在城市移動,甚至在城市中,你可以看見小小的菜圃,種著日常需要的蔬果。
這簡直是社會學家眼中的「烏托邦日常」。老師說,朋友告訴她,150 年前,有一群知識分子用自己的力量,走入菜園、提倡用本土的丹麥語,轉譯學院用拉丁文寫的艱澀知識。這樣的工程很浩大、漫長,但漸漸地,公民用知識和行動,廢除了丹麥的專制體制。
我記得老師勉勵大家,每次想到這,她總是告訴自己「哦,原來需要 150 年呀!」
社會學讓我能夠相信「行動是有意義的」,不被失敗主義淹沒;同時讓我面對對立的意見時,能夠快速地切換、同理。
這段文字的收尾,我想用何明修老師曾引用德國學運領袖Rudi Dutschke的話,提醒改變社會要透過「體制內的長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
這正是社會學最迷人的地方——在運動的激情之後,我們走在杜鵑花節所說的「超廣出路」(不同職業)上。在社會體制內的不同崗位上,成為行動者,讓改變我們的社會學,也能改變社會。
感謝社會學闖入我的生活,讓我在沮喪的時候,仍能提醒自己見樹又見林;在面對失敗時,能夠安好地說「謝謝指教。我要繼續往前走了,一起嗎?」

(文章轉載自:張育萌 2025/1/6 臉書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