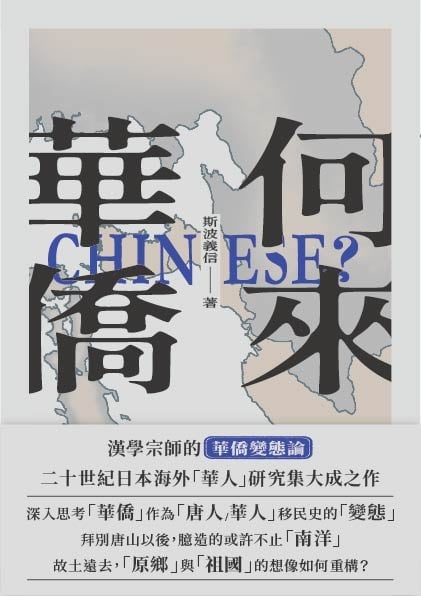什麼是「僑」及其當代關聯
——《華僑》中譯本代序(更新版)
陳弱水
陳健民先生翻譯斯波義信教授《華僑》一書即將出版,我曾在臉書上發表有關「僑」觀念的短文,一八四一出版社認為該文會對本書的讀者有幫助,希望轉載於書中,或由我另外寫序。我閱讀書稿,感覺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可能是修訂原來的文章,加上些許呼應斯波教授書的內容,至於題目,只添加副題。這就是本文的緣起。
「僑」是特殊的字。它廣泛使用於中文和華語,但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存在。在描述的層面,「僑」是指從A地遷居到B地或這樣的人。但「僑」有更強的意涵,它往往指從A地遷到B地,從A國遷到B國,但認同仍在A地與A國,「僑」和他們的後代本質上是A人,B地與B國只有工具性的意義。就近現代而言,「僑」的現象──認同在祖鄉而不在生存所託的社群和國家,在台灣和東南亞都很明顯——雖然未必有「僑」的名義,往往也是這些地方緊張與分裂的重要來源。
可能大多數讀者不曾意識到「僑」這個字和觀念的獨特性,這裡要多做點說明。「僑」的特殊性反映在它是不可翻譯的。在我所知的世界主要語言,都沒有這樣的概念。如果我們把「僑」輸入翻譯軟體,英文是Overseas Chinese,法文是Chinois d’outre-mer,德文為Auslandschinesen,日文則出現「華僑」。簡單說,「僑」就是海外華人,「僑」和「華僑」沒有差別,這個字沒有獨立的意義,在其他語言無法(或極難)找到對應。有時為了方便,我們會說類似「美僑」、「僑居在台灣的比利時人」的話,但這裡的「僑」只代表移居外國,跟英文的expatriate一樣,並不意含移居者與母國的聯繫,也難以適用到移居者的後代。事實上,作為動詞,expatriate有疏離母國或從該處放逐的意味。
這種獨特,幾乎毫無普遍意義的詞語是很罕見的,我可以舉個例子來做對照。漢人文化中的「孝」是特別的觀念,與其他文化中有關親子的情感和想法相當不同,但即使如此,一般不會把「孝」當作無法翻譯的詞語。「孝」的英文表述是filial piety,這雖然是為漢人式對待父母之道量身打造的,至少可以讓異文化人士據以想像一種特殊的親子觀。「僑」就更像文化地圖中的孤島。
「僑」這個字和觀念是怎麼來的?先談字。「僑」原來根本沒有遷居的意思。東漢《說文解字》說:「僑,高也。」「僑」的意思是「高」,從「喬」演化而來,加上人字邊,讀音不變。從古文字資料看來,「僑」字大概戰國才出現。在傳世的先秦文獻,「僑」主要用於人名,鄭國子產的名就是「僑」,《左傳》中還有舟之僑、叔孫僑如等,這些原本應該是「喬」,「僑」是後世的隸定(即回溯性地將某字改寫為另一形體)。「僑」是「高」,「僑如」是「高高的樣子」,顯然在古代被認為很適合當作名字。「僑」有遷居或遷居之人的意思,現存文獻中,最早的紀錄在戰國末的《韓非子》,但接下來要到三國(公元三世紀)才看得到,並不是常用字。
「僑」為什麼會冒出「遷居」的意思?來源明顯是《詩經.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一個神聖文本中文學性的描寫,讓高高喬木的「喬/僑」和遷徙發生了關聯。換句話說,作為遷居意義的「僑」,不是來自自然的語言,不是人講出來的,而是高層士人挪用《詩經》中的表達的結果,應該是先出現在書面語,再流傳到口語。
遷徙意義的「僑」本來只是客觀描述,可見於今天仍在使用的「喬遷」。「僑」進一步可意味雖然遷到某地,但認同或本質性的存在仍寄託於祖鄉,顯然發生在四世紀初。當時中國北方發生大動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以洛陽為中心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到江南重新建國,史稱「東晉」。這些貴族力量(歷史學一般稱為「士族」)以「僑」來界定自己和追隨者的身分。這些北方士族擁有至高的政治社會地位,他們不改籍貫,希望永遠是祖鄉的人,以祖鄉為家族名號(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太原王氏)。東晉朝廷和統治者設置「僑州」、「僑郡」、「僑縣」,收納北方來的民眾,戶籍不同於本地人,而且享有免除徭役和賦稅的優待。僑郡縣雖多設於長江沿岸,但都使用北方的地名,甚至有一個南方行政區同時存在幾十個僑郡縣的情況。這個以北方「僑姓」士族為首的僑居現象,延續了兩、三百年,是後世「僑」觀念的源頭。
對於這個現象,中國中古史大家唐長孺(1911-1994)有所解釋。唐先生指出,這是新生事物,漢末大亂之後,在東南立國的孫吳已經有很多北方來的流寓人士,這時約在東晉建國前一個世紀,但並沒有類似東晉僑人的心態,他們居留一段時期後就落籍江南,成為當地人。他又說:「本來,漢代改籍是頗為常見的,那種高標郡望,不願附籍所居州郡的風氣只能出現在士族門閥形成之後。」(〈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51-52)唐先生的意思是,東晉以下的新僑居本質上是位階現象,是遷移來的人認為自己高於遷移地,要當永遠的旅人,把自己和子孫定位於祖鄉。在漢末、三國之際,貴族階層尚未穩定形成,北方高層士人的優越地位還在浮動中,但西晉以後,主要由於九品官人法的作用,士族世襲化,成為貴族(aristocracy)的形態,這是東晉統治者強烈高階感的來源。
歸結而言,大概在漢末,中國開始使用「僑」來指稱遷居,原來遷居並沒有特殊的文化意義,遷居者都以落籍為歸宿,但在東晉初,以貴族為領導者的移民遷到南方,出於優越的心態,他們把「僑」的身分制度化,將自己定位為在南方的非南方人。我們從「僑」現象的起源認識到,這個觀念並不是簡單的懷鄉念祖,而是與遷居者的自我意識關係密切──他們是高階的,他們所在的地方沒有認同的價值。
近現代又是各種「僑」現象大爆發的時代,例如東南亞和美國的華僑、台灣的「外省人」,與中國中古早期南方相比,近現代「僑」意識的背後增加了族群優越感、天朝觀念和中華民族主義等因素。近現代的「僑」現象當然不能說是「僑」這個字所帶來的,關鍵應該是在上述的高位意識與民族主義執念,但「僑」的意識為遷居者的這種心態提供了定型和延續的工具,也方便了原居國的擴張。「僑」具有迷惑性,很容易讓人覺得它不過是移民(immigrant)或遷居外國者(expatriate)的中文用語,它遠不止此!它是獨特的。
現在轉到斯波教授的書。這是一本通論性著作,敘述和討論12-13世紀(約當中國宋元之際)以後中國東南人士移居海外的歷史,以17世紀後為主。書名「華僑」,是取這個詞語的描述意義,等同於海外華人,跟前面所談的「僑」不同。斯波教授指出,「華僑」是新名詞,起於1880年代,1890年代變得普遍。斯波教授的根據是政府和士大夫的文獻,我查了一下上海《申報》資料庫,發現1870年代就有使用,但要到二十世紀初才常見,看來民間流行更晚。總之,這是很晚才出現的說法,但很快成為重要概念,除了反映中國人在近代大量出國,也和晚清政府重視這個問題以及移民現象議題化有關。
斯波教授也指出,「華僑」一詞可有與母國聯繫的涵義,不僅是一般移民而已。他把近代東南亞華人分為三類:「華工型」、「華商型」和「(愛國)華僑型」,這個分類就透露出「僑」觀念的特殊性了。斯波教授說,三類之中,「華商」是主體,「華工」和「華僑」都屬邊緣。整體而言,海外華人現象有其複雜性,華人/華僑的屬性在不同地域或國家有差異,最主要的因素是移居地的狀況,由於移居地往往是殖民地,殖民者的政策也有影響。此外,中國本身的情勢和作為也相當重要。關於海外華人,不但「華僑」一詞出現晚,「僑」的性格也是19世紀末才開始浮現,這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密切相關。中國的政治勢力也有意識地塑造僑民。在成立於1913年春天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參議院有6位華僑代表。這是世界允許海外移民參政的首例,顯示近代「僑」意識的復活帶有很大的動能。
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大家所寫的海外華人通史,涉及八百年來這些人群的複雜演變和多種面貌,很值得閱讀。這段歷史中,「僑」現象在近代的興起是重要的一環。旗幟鮮明心繫故土的「僑」雖然只占華人與華裔的少數,「僑」意識恐怕分布很廣,「華商」、「華工」中也有。華人的「僑」面向不純是歷史問題,它仍是今後東亞國際局勢中的重要變數,是必須了解和關注的。
照片說明:
斯波義信著作中譯版《何來華僑》封面